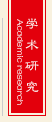挟书律研究
发布人:中国秦文研究会秦文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5-06-24 10:42 点击率:2626
李 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秦“焚书”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有关此事件,仍有许多未解之迷,以致学界众说纷纭。譬如挟书律的内容是什么,萧何是否收书,博士官是否可以藏书,诸子书是否被焚,秦人何以引诗书等等。本文依据前贤时哲的研究,指出挟书律可以复原为“丞相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在复原挟书律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史记、《诗》、《书》、百家语的差别,称引百家语的原则,秦是否焚民间的诸子书等问题,以及其它与学术史相关的问题。
秦之“焚书坑儒”,是关系到中国古代学术的一件大事。秦汉之际的学派问题,也与之很有关系。然而与焚书相关的事,则仍然有不少疑义。
比如焚书的范围,王充在《论衡·正说》中讲“唯博士官乃得有之”,朱子说:“如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1]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也说:“《诗》、《书》、百家语之在人间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2]。萧参《希通录》则又谓“天下之书虽焚,而博士官犹有存者。惜乎入关收图籍而不及此,竟为楚人一炬耳,前辈尝论之。”[3]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说“秦之焚书,焚天下之人所藏之书耳。其博士官所藏,则故在。项羽烧秦宫室,始并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以后之学者咎萧何不能于收秦图书之日并收之也。”[4]萧、胡之论,表明其前之学者多认为秦不焚博士官之书,而导致经籍亡佚的罪过,逐渐转移到了萧何、项羽身上。此后持相近论点者犹多[5]。据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一及方回《续古今考》卷六、二十九所载,吕东莱曾说:“萧何独收图籍而遗此,惜哉”,则首咎萧何者当为吕东莱。
但是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则标举《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之义,以“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为刘歆之伪说,是刘歆遍伪群经之借口[6]。康有为之说,影响很大。连启发了康氏的廖平都反受其影响,将其说写入《古学考》之中[7],以致一时之间康、廖二人到底谁影响了谁都曾有过争论。后来廖平的弟子蒙文通先生在《经学抉原·焚书》篇中,细数秦廷称引六艺经籍之事,认为“孔子之术,诚不因坑焚而隐讳,亦不待除挟书之律而显明。”[8]
然而章太炎先生认为王充所说“博士独有其书”是误解,郑樵、马端临“沿袭斯论,遂为今日争端”[9]。顾实先生则举伏生壁藏《尚书》之事,认为博士亦不得藏书[10]。
于是关于秦焚书,就有了秦博士官是否可以存书、萧何是否收秦经史子籍以及项羽是否焚书等诸多问题。秦焚书还与《挟书律》等问题相关。前辈学者如钱穆、钱钟书等对有关问题有不少好的意见[11],浅学思之经年,敢献愚虑以待高明指教。
一、挟书律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仆射周青臣进颂,却引来博士齐人淳于越的批判。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言曰: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其后是“制曰:‘可。’”这是有关秦焚书之事的详细记载,小有不同者还可参见《史记·李斯列传》等。后人论及焚书之事,常提到《挟书律》。关于《挟书律》,后人常称引《汉书·惠帝纪》所记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除《挟书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挟,藏也。”又引张晏曰:“秦律敢有挟书者族”。因此后人以为《挟书律》的内容是“敢有挟书者族”[12],此文被收入《九朝律考》等书,至今不少教科书解释《挟书律》也仍然据之为说。
但是李学勤先生将上引李斯文和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津关令》比较,指出秦律令的制定有一种形式是对奏书予以认可,并比较了李斯语中和秦律相近的言语,指出李斯之言自“臣请”下面就是律文[13]。现在张家山汉简《津关令》已经公布,其律令形式是:
一、御史言,越塞阑关,论未有□,请阑出入塞之津关,黥为城旦舂;越塞,斩左止(趾)为城旦;吏卒主者弗得,赎耐;令、丞、令史罚金四两。智(知)其请(情)而出入之,及假予人符传,令以阑出入者,与同罪。非其所□为□而擅为传出入津关,以传令阑令论,及所为传者。县邑传塞,及备塞都尉、关吏官属、军吏卒乘塞者□其□□□□□日□□牧□□塞邮、门亭行书者得以符出入。·制曰:可。
□、御史请诸出入津关者,诣入传□□吏(?)里年长物色疵瑕见外者及马帜(识)物关舍人占者,津关谨阅,出入之。县官马勿帜(识)物者,与出同罪。·制曰:可。[14]
比较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根据李学勤先生的意见,我们或可大致复原秦有关焚书的法令是:
丞相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李斯所言文字中没有“挟”字,只有同义的“藏”字,所以李先生怀疑“李斯所言诣守、尉杂烧,系指当时集中施行的措施;挟书者族,则是法律中长期生效的内容,《挟书律》之名当即由此而生。”[15]李先生取调停之说,是很审慎的。
但是我们或可怀疑张晏之语仅是大略称引《挟书律》的内容(李斯之言),并非是另有所谓《挟书律》,《挟书律》应该就是上面所复原的法令。因为“敢有挟书者族”这一句话不明确、不具体,对于“书”没有具体规定,很难操作,这不可能作为法律,只能看作是对李斯之语的简单概括。类似的概括之语,还可见《论衡·正说》所说:“有敢蔵诸书百家语者刑”。此外如《太平御览》卷637:“如淳曰:秦始皇令敢有挟诗书偶语者俱为城旦也”,卷646“《史记》曰:秦皇平六国,制天下藏诗、书及偶语弃市”,卷652 “《汉书》曰:惠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如淳曰:秦皇令,敢有挟持书偶语者,为城旦舂。)”
李斯之言,前辈学者早已指出其目的是禁止以古非今,其罪至灭族;私藏《诗》、《书》、百家语的罪行均相对较轻[16]。而秦始皇既批准了李斯的动议,它具有法律性质,应该得到了比较有力的推行。坑儒之事前,秦始皇就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基本上是令行禁止,他似没有必要又以更重之罪罚“敢有挟书者族”来强调其事。至若李斯之言并无“挟”字,观郭璞注《尔雅·释言》“挟,藏也”所说:“藏,今江东通言挟”,可知“挟书律”之“挟”字,很有可能是后人运用方言而称呼之,秦律原名或未必就称为“挟书律”。因此,汉代的《挟书律》之所指,就是上述据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所推出的内容。其原文,是以李斯的奏议加上“制曰:‘可’”的形式颁布的法令。张晏之语,应该只是略举其要。下面为讨论方便,径以《挟书律》指上述复原的法令。
基于《挟书律》,我们可以进而讨论一些复杂的问题。我们容易明白,《挟书律》所明令禁止挟藏的,是史官所藏的秦记之外的史记;博士官职掌之外的《诗》、《书》、百家语。这表明,秦廷确实允许史官、博士官拥有一定的书,古来的传统说法并没有错。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司马迁所见“独有秦记”,这表明秦确实烧毁了秦记之外的许多史书,说明《挟书律》确实得以严厉实行。太史公同时也说有一些人私下藏了些《诗》、《书》,得以在废除《挟书律》之后重见天日。私藏之事,在历代毁禁书籍的事例中屡见不鲜。但是司马迁这句话容易引起歧义,他没有明言是否见到秦朝博士所在的官府有藏书。
因此顾实先生举伏生藏《书》以及孔壁藏书的例子,又据《史记·六国年表》之“《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以说明“博士官不能在秦廷藏《诗》、《书》、百家语”。顾实先生还考察秦博士,指出多文学方术士及名家人物(黄公)[17],以证成其说。
但是马非百先生指出:“博士官所职与博士所职不同,前者指机关而言,后者则为私人”,顾实是“误机关与私人为一致”[18]。马先生之说可信。因此,博士官所在的官府,可以收藏《诗》、《书》、百家语;但是博士却不能私人自藏《诗》、《书》、百家语,因此才有伏生不得已而壁藏《尚书》之事。而且我们不能否认秦廷博士之中多儒生,譬如博士中有伏生及其师李克,还有羊子(《汉书·艺文志》列入儒家)。《史记·封禅书》记载说:“(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此处之“儒生、博士”,可以猜想儒生是以待诏博士之身份参与封禅之事。叔孙通、鲍白令之很可能都是以文学(方术)被征,待诏博士[19],随时可以因幸被补充为博士,如叔孙通。顾实先生之说,恐怕是为了反驳康有为“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之说而持论太过。
至于章学诚以李斯所说“以吏为师”即学在官府之旧例,就是以博士为师之说,则驳之者已多,不必详论[20]。
二、《诗》、《书》、百家语
《挟书律》所禁的书,很明显是史记(非秦记之史)、《诗》、《书》、百家语,然尚有数事可说。
其一,史记、《诗》、《书》、百家语有区别。
对于史记,即使是史官所藏的非秦记者,也要焚毁;对于《诗》、《书》、百家语,则允许博士官收藏于官府;但是,“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则《诗》、《书》即使不烧,可藏于特别的官府,也不可偶语,而百家语尚可以谈说、称引,故《诗》、《书》比百家语容易惹祸。相对而言,博士官府藏有诸子百家书是比较保险不会出问题的,只要不以古非今。
与秦有关的《诗经·秦风》、《尚书·秦誓》,或也在严禁之列[21]。像《左传》记有部分秦事,汉代由张苍献出,看来也是先藏而后出,说明即使有部分关系到秦之历史者,也在严禁之列。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从赵氏一部分人和秦王政有关推测,或许赵都邯郸的记录也被视为与秦国间接相关的资料了吧……赵敬侯以后的邯郸记录能得到保存,流传到汉代”[22],还有待研究。
其二,百家语可以称引,惟不能以古非今。
《挟书律》说“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对于百家语则无此严禁之语。是故我们可以明白《史记·李斯列传》记胡亥以韩非之言问李斯,李斯则以申子、韩子之语以阿胡亥之意,并非因特权而超出《挟书律》之外。或疑《史记·乐书》尝载李斯进谏:“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似乎六艺仍受重视。但此处祖伊所言的“诗书”,或有所指;况且李斯并未称引任何文字。又观前述李斯奏书之言,所谓“以古非今”,主要是“非上之所建立”,“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是对于法令制度的非议,所以李斯进谏之语并未违反《挟书律》。
蒙文通先生曾举“蒙恬说《金縢》之传,蒙毅陈《黄鸟》之说”,以证“孔子之术,诚不因坑焚而隐讳。”所举两事,俱见《史记·蒙恬列传》。然而蒙毅未明引《黄鸟》,所说“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或本无“三良而死罪”五字[23],故所言未必是《秦风·黄鸟》;蒙恬所述周公言行与《金縢》有差别,虽引有“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不见今《尚书》及《逸周书》),但蒙氏兄弟俱为临死前与使者之语,并非上书陈情。又蒙毅之语尚有“故曰:‘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于无辜’”,当为百家之语。
其三,秦焚民间的诸子书。
至于《论衡·书解》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赵岐《孟子题辞》曰:“(《孟子》)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刘勰《文心雕龙·诸子》记:“烟燎之毒,不及诸子”,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载:“《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鬻子序》言:“遭秦暴乱,书、记略尽。《鬻子》虽不预焚烧,编秩由此残缺。”不少学者遂谓秦不焚诸子书,恐怕有所误解。秦只不过是允许博士官藏诸子书。前文已说明,相对于史书、《诗》、《书》而言,诸子书的风险要少。司马迁谓“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孟子题辞》和《孔子家语后序》是说“得不泯绝”和“不见灭”,但是《鬻子序》说到“编秩由此残缺”,诸子书的情况比史记要好一些而已。《论衡·书解》则是相对于五经之残缺而说“诸子尺书,文篇俱在”,《文心雕龙》之下文便立即说到刘向校诸子书“杀青所编,百有八十余家矣。”因为汉代尚可见到不少诸子书,而《诗》尤其是《书》残缺很多,故相对而言,诸子书没有焚尽,但是也有不少毁损。马端临就说过:“《荀子》载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弟子问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扬子》载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今书皆无之,则知散轶也多矣。岐谓秦焚书,得不泯绝,亦非也。或曰:‘岂见于《外书》邪?’若尔,则岐又不当谓其不能弘深也。”[24]因此秦并非不焚民间的诸子书,只是因为诸子书尚可存于博士之官,且可以称引,故相对保存较好,但是也因为焚书而有不少散佚。
其四,“百家语”包括诸子百家之子书、传记。
俞敏先生曾据《论衡·书解》记载秦不焚诸子书,认为秦所欲焚的“百家语”之“百家”,不是指诸子,而是指“纵横之术”[25]。这一观点恐怕不可靠。前面已经解释了《论衡·书解》说“诸子尺书,文篇俱在”的原因。古代“百家”之称多见,多指诸子百家,似不见特指纵横家者。
“百家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儒家传记及子书,秦虽不禁卜筮之书,但是儒家解说《周易》的传记却属于百家语,也在焚禁之列[26]。是故马王堆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有不同,尤其是帛书《二三子问》、《衷》、《要》《缪和》、《昭力》等篇,几乎不见于后世载籍;帛书《系辞》与今本也有所差别;而汉初数《易》的传承,也只有商瞿一系可考。这些结果,当都和《挟书律》禁百家语有关。因此,《易传》等书也是在严禁之列的。不少学者以为儒家因秦不禁《周易》才假托孔子名义传《易》,《易》到秦末才列入儒家的六经,恐怕对于《挟书律》的理解有问题。现在战国中期郭店楚墓出土的《六德》和《语丛一》中已经出现了包括《易》在内的六经名称,犹可见此说之误[27]。
其五,秦不禁礼乐,但禁百家有关学说。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秦始皇死后,群臣正七庙之制。这都是秦朝兴礼乐的情况,其制礼作乐是要垂范后世,如秦始皇二十六年改周舞之名为“五行”。秦不禁礼乐,应该会允许礼乐之官有一定的书籍(汉初之礼乐,“大氐皆因秦旧事焉”[28],叔孙通多主其事);却并不意味着儒家的《礼》、《礼记》、《乐经》、《乐记》等可以流传。《挟书律》主要是防止人“以古非今”,自然也不许人据礼乐“以古非今”。而且《礼记》、《乐记》属于百家语的范围,是故河间献王因得不到《乐记》,才有《汉书·艺文志》所说“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之事[29]。司马迁在《乐书》中虽抄有部分《乐记》,但是不完全,有可能是采自《公孙尼子》、《荀子》等书。刘向校书,才得到二十三篇《乐记》。因此,虽然秦律、《挟书律》不禁礼乐[30],但是蒙文通先生据秦制礼作乐之事,欲说明孔子之术不因坑焚而隐讳,恐怕有所偏差。
其六,因焚书而古书一度口传。
古代学者常有一个说法,认为古代用竹简抄写之书籍,贵重而稀少,故多是口传,到汉初才著于竹帛。现在据战国时出土之典籍来看,并非如此。看来当是因为《挟书律》,才使得有些书只能以口传的形式流传。比如非秦记之史,尤其是《春秋》及其传。是故汉初《公羊》犹口传,至汉景帝时才由公羊寿和其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说到《公羊传》,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叔孙通列传》记陈胜起兵山东,二世召博士诸生问。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文献通考》引郑樵之语认为“皆引《春秋》之义以对”,蒙文通先生也说这是“博士申无将之训”[31];顾实先生则说这是不敢言《春秋》之义,二说正相反。他们所指的《公羊传》,在庄公三十二年、昭公元年并云“君亲无将,将而诛焉”,和上述博士之言尚不同,到底是不敢言《春秋》之义,还是引用其义,还有待研究。
其七,秦是否允许民间士吏藏秦记及杂抄文辞,尚有待考察。
近年出土的秦墓之中,确实少见《诗》、《书》、百家语,多为律令及日书。但是不少秦墓的年代并不明确(湖北沙市周家台秦简是比较明确的在《挟书律》颁布之后入葬的竹简),惟云梦睡虎地秦简中除律法之外尚有《编年纪》与《为吏之道》,年份相对较明确。《编年纪》记近百年秦国大事兼及小吏喜的部分事迹,仅计年份及大事,可能是抄自某种《秦记》。但是一般认为墓主便是《编年纪》中的喜,而《编年纪》止于秦始皇三十年,喜当死于此年,尚未到颁布“挟书律”之年。《为吏之道》与王家台秦简《政事之常》有相近内容,属于杂抄,学界喜欢讨论其中部分文句可见某一子家的思想。因此,秦是否允许普通士吏传抄秦记以及像《为吏之道》这样的文章,尚有待研究。
三、杂论
秦朝严刑峻法,《挟书律》的推行应该是比较严厉的。当然,会有不少人私藏《诗》、《书》百家语;但是私藏不能保存所有重要典籍。《史记·儒林列传》就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许多学者认为《挟书律》应该是到了陈胜、吴广起义就基本废止了,故认为其推行不过只有五年时间。此说有一定道理,《史记·儒林列传》记:“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刘邦也和咸阳民众约法三章,不问挟书律了;而且陆贾时时在刘邦面前称道《诗》、《书》。
但是,汉多承秦法,而《挟书律》到汉惠帝四年才正式废除,这也就是说没废除之前,它仍然有法律效力。李学勤先生就曾指出:“看近年各地发现的简帛书籍,战国时期经子多见,到秦以至《挟书律》初废的吕后时,出土的均符合律文所许可,直至文帝初年,情形才有改变,如长沙马王堆帛书,阜阳双古堆竹简等。”[32]张家山247号墓汉简大约下葬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或之后不久,其中有《盖庐》,属于兵法,或可称为例外。不过汉初张良、韩信就曾整理过兵法,则兵书或早就不在受限之列[33]。项羽妾冢曾经出土过《老子》,然不知其确切下葬年代。《古文四声韵》卷二收有三个出自“古老子”的“常”字,却未收“恆”字,有可能是汉文帝时期的抄本,避“恆”字讳(但是《古文四声韵》卷二有出自“古老子”的“盈”字,则或不避汉惠帝名讳)。
《挟书律》的实行,对于中国学术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虽然有一些学者冒生命危险保存了一些书籍,但是它仍然导致古史茫昧,六艺残缺,百家往而不返。据此我们或不难推知,萧何入咸阳收书,并没有专门收史官、博士官所掌的图书。萧何所收图书范围,《史记》、《汉书》均讲得很明白。假若萧何曾收博士官所掌之书,则六艺当不致亡缺很多。
康有为《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之说,恐过于武断。一者太史公明言萧何所收为律令图书,无关经史子籍。《史记·萧相国世家》说萧何收图书之效:“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后来萧何更定汉律九章,当也是根据所收律令图书。二者康有为谓萧何在丞相府所收为李斯所领之图书,羌无故实。李斯被赵高谋害之后,赵高继为丞相,萧何所收者当为“申法令”之赵高所存图书;即便有李斯所藏图籍,此人倡议焚书,恐亦不便多收留六艺经籍。《汉书·酷吏传》载:“(严)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由此可知丞相府主要收藏律令,故可以学法律。三者康有为过于轻视秦法“城旦”之刑,云“即不焚烧,罪仅城旦,天下之藏书者犹不少”[34],不知城旦为四年期劳动苦役;而且《挟书律》之对象,主要为识文断字的士人和胥吏,这些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虽然高爵者尚可削爵减刑),绝非轻视城旦之刑而勇于冒险者。
此外康有为还曾经提到张苍曾为秦御史,掌柱下方书。不过康有为没有讨论萧何所收御史书的问题。关于“方书”,后世有不同的解释[35],似以官府文书近是[36]。《史记·张丞相列传》说:“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由此可知柱下史(御史)书的范围。我们不宜以老子曾为柱下史,以及张苍曾献《左传》,遂谓柱下方书为经子典籍。蒙文通先生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云“御史大夫,秦官……有两丞……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以证张苍所掌为古文旧书[37]。然而藏中秘之书的天禄阁、麒麟阁,皆为萧何监造。不难理解兰台秘书之设,亦是汉世造作,只不过御史大夫之名沿袭秦制而已,不得以汉代之御史中丞掌秘书,以证秦代御史也掌古文旧书。而且,秦官府藏书当是小篆或隶书抄写,恐不会是东方六国的古文。
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说《孔子家语》因“高祖克秦,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然而并没有具体说是不是萧何抑或他人收集《孔子家语》(汉高祖本人当不会亲自做此事),也没有说是不是得自于史官、博士官府。倘为博士官所掌者,应该为秦小篆或隶书所写,又有许多重文可以对照,似不应该有很多古文字[38];故很有可能并非是博士官所掌者,而是民间藏书。孔安国的《孔子家语后序》,昔人疑其伪造,还有待研究[39]。
又汉兴后孔安国所得古文《尚书》五十六篇,而王充在《论衡》中的《佚文》、《正说》两篇均提到汉成帝有百篇《尚书》之事。论者或以此为中秘《尚书》,以证“《书》固未尝亡”[40]。然此两篇亦记魯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百篇,当即成帝之百篇《尚书》。而刘向、班固等皆说孔壁《尚书》为五十余篇,故阎若璩以为王充得于传闻,不可据[41]。但是《汉书·艺文志》确有不载之中秘书,其尤者为古文《易》,如《汉书·艺文志》明明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但是却没有在《易》下写出古文《易》。不过《汉志》不录古文《易》,有可能是因为它“与施、孟、梁丘三家经无篇章、卷数的不同,虽然与立于博士的三家经文偶有文字的不同,无关乎经说,故不著录于《艺文志》”[42];更可能是《别录》/《七略》有不同,如今存刘向《别录》佚文有《楚辞》、《老子》等书的《叙录》,其书却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刘歆对《楚辞》可能有新编排,至于《老子》,或说作《七略》时,中秘所藏时无其书),是故不能以《易》之例证王充之言。
余嘉锡先生认为萧何有可能收集了兵法[43]。但是此说尚缺少佐证,或亦可谓张良、韩信入关后收兵法,其后遂继以校书之事。如此则其他个别官员也有可能收集其它书籍。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余嘉锡先生谓指“秦时国家所藏之书散乱失次”[44]。则司马迁“紬石室金匮之书”,就是曾看到了这些藏书,他也多次提到《秦记》[45]。又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但是所得遗文古事没有说明具体来历,以及何人所收。恐怕不是“刀笔吏”萧何,有可能是其他官员战乱间断续为之,故致六经残缺。司马迁没有说项羽火烧咸阳与“石室金匮之书”的关系,是故我们不宜将古籍残缺不归罪秦始皇、李斯而归罪项羽。而且即便项羽火烧宫室,“石室金匮”也尚可稍微防患[46],不比秦之专门点名焚书。
[1]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8,第3277页。
[2] (元)马端临:《总叙》,《文献通考·经籍考》卷1,第8页。
[3] (元)萧参:《希通录(及其他一种)》,“丛书集成初编”2889。
[4]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7,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4页。
[5] 参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6-41页。
[6] 康有为“秦焚六经未尝亡缺”之说,或是依郑樵《通志·校雠略》之说而来。《史记·萧相国世家》说“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郑樵于是说:“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康有为遂谓萧何收得六经。
[7] 廖平:《古学考》,《廖平选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25页。
[8] 蒙文通:《经学抉原》,《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57页。
[9] 章太炎:《秦献记》,《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9-71页。按:王充原文是“唯博士官乃得有之”,章太炎引为“博士独有其书”,有不同。章太炎所作《秦献记》、《秦政记》,有特定思想背景,不可视为考史之作。
[10]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5页。
[11]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版,第258-263页。
[12] 实际上,古书中尚有其它不同说法,如《太平御览》卷637记:“如淳曰:秦始皇令敢有挟诗书偶语者俱为城旦也。”卷646:“《史记》曰:秦皇平六国,制天下藏诗、书及偶语弃市。”卷652“《汉书》曰:惠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如淳曰:秦皇令,敢有挟持书偶语者,为城旦舂。”
[13] 李学勤:《从出土简帛谈到〈挟书律〉》,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研究》,第一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
[14]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3、84-95页。
[15] 李学勤:《从出土简帛谈到〈挟书律〉》,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研究》,第一册,第4页。
[16]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188页。
[17] 顾实先生还谓秦有占梦博士,恐不当,参徐复:《秦会要订补》及《附录》所收金少英《秦官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476页。
[18] 马非百:《秦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96页。
[19] 施之勉先生根据《说苑·至公》云“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之文,以为鲍白令之非博士。马非百非之(见氏著:《秦集史》,第899页)。钱穆先生引蒙文通之说以鲍白令之为秦博士(见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193页)。
[20] 参徐复:《秦会要订补》,第138页;李学勤:《从出土简帛谈到〈挟书律〉》,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研究》,第一册。
[21]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已提及:“今下令焚《诗》、《书》,而曰‘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则《秦誓》、《秦风》亦秦记也,独非《诗》、《书》乎?”见(元)马端临:《总叙》,《文献通考·经籍考》,第7页。
[22] [日]藤田胜久著,曹峰、[日]广濑薫雄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第292页。
[23] [日]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第1587页。
[24]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11,第293页。
[25] 俞敏:《说“百家语”》,陆宗达主编:《训诂学研究》,第一辑。
[26] 参李学勤:《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文物》,1994年第1期。
[27] 参廖名春:《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学说的方法论问题》,《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
[28] 《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