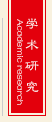转发|聚落与交通视阈下的秦汉亭制变迁(一)
发布人:中国秦文研究会秦文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7-05-31 09:34 点击率:3534
聚落与交通视阈下的秦汉亭制变迁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王彦辉
摘 要:秦汉文献中的“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是真实存在的制度设计。亭的设置原则一是不能远离聚落,二是不能脱离交通。邮亭主要设置于京师与郡国、郡国与县邑的主要交通沿线,乡亭主要设置于聚落附近和郡国辖域的次级交通道路。乡亭、邮亭的辖区称“亭部”,亭部中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耕垦的需要逐渐形成新的聚落,此即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和三国吴简中的“丘”。新的聚落称“丘”而不称“里”,说明“丘”是按地域命名的,而非乡里行政组织。丘的形成既有邑居之民外迁的路径,更有移民在国家赋民草田、赋民丘地等安置政策下通过“占垦”而聚居的渠道。随着东汉地方管理体制的变动,亭部开始对辖域内散居的聚或丘行使乡部治权,出现亭部一丘的隶属关系。亭部退出历史舞台后,丘划归所在乡或另设乡统一管理,形成乡一里、乡一丘不同的管理体系。秦汉以来以联户为目的的乡里组织在聚与丘的浪潮下逐渐松动,聚落逐渐演变为地域单位,表明国家对丘的管理已经放弃了以“里”为基础的乡里编制和多重监管的传统。乡里行政编制虽然犹存,但乡村行政权力弱化的历程已经开始。
秦汉时期的“亭”有不同类型与职能分工,承载着社会治安、文书传递、分部理民等职任,在地方行政、司法监察和聚落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两汉志对县乡机构的记载过于疏略,纪传部分虽有一些传主担任过亭长之类的起家官,可史家记述其生平事迹时往往一笔带过,从而使亭与乡里体系的关系及其演变轨迹一直雾里看花。史学前辈曾对此钩沉索隐,试图厘清乡、亭的关系和史书记载的冲突,但其中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近年来公布的简牍资料又派生出新的话题,比如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亭与丘、三国吴简中的乡与丘等,“亭”在乡里行政管理制度演变中发挥了何种作用?这些问题由于新材料的公布或许为我们做出新的诠释提供了线索。
一、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与县面积
秦汉文献及简牍资料所见的“亭”,名目繁多,诸如都亭、街亭、市亭、门亭、乡亭、邮亭、田亭、燧亭、野亭等,从亭的设置地点划分,可简化为城邑之亭和乡野之亭两大类。为使行文避免概念繁杂带来的烦恼,暂以“乡亭”指称内郡国邮亭之外各种名称的乡野之亭。学界对城邑之亭如都亭、街亭、门亭、市亭的性质及其功能经过讨论已无异议,唯乡亭与邮亭的设置及其与乡里制度的关系一直歧见纷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对史书所记乡、亭、里之间的统属关系存在不同理解。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1]
刘昭注《续汉书·百官志》引《风俗通》曰:
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2]
按《汉书》的叙述逻辑,古代史家一般是把秦汉乡亭里的递进关系推导为积里为亭,积亭为乡,积乡为县,即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而《风俗通》又说“十里一乡”,两种说法虽仅一字之差,却失之千里。班固、应劭同为东汉人,他们的说法难以撼动,所以历代正史典制并未对此产生怀疑。顾炎武虽然指出汉代制度是“以县统乡,以乡统里”,[3]而对乡里亭究竟是“十亭一乡”,还是“十里一乡”亦未置一词。
20世纪30至50年代,中外学者围绕汉代乡里亭问题展开持续讨论,基本观点可大致归纳为三类:“道里”说,“亭部之里”说,“亭与乡里不同性质”说。[4]80年代以来,由于简牍资料的陆续发现,这个话题重又成为研究的焦点,总之,前人的研究在思路上大体是沿着以下两条路径展开的。
一是改字解经的路径。学者或据《风俗通》的说辞判定班固的“十亭一乡”之“亭”为“里”之误篡,或据《太平御览》引《风俗通》测度《续汉书》刘昭注存在漏文或误引,从而理顺《汉书》所述乡亭里之间的关系。此说由王毓铨先生首开其端,认为汉代的亭属于治安系统,乡里属于行政系统。“十里一亭”之“里”为“步里”,“十亭一乡”之“亭”当为“里”之误篡。熊铁基先生亦认为“十亭一乡”是“十里一乡”之误,“十里一亭”和“十里一乡”都是管理里落居民的机构,一个管理乡村居民,一个管理城镇居民。[5]冨谷至则认为《续汉书》刘昭注或许存在漏文或误引的可能,“十里一亭”的亭指邮亭,“十亭一乡”的亭则包括乡亭、田亭、水亭、仓亭等。一乡之中平均包含了十个亭。[6]
改字解经说的最大贡献是在乡里亭的纠缠中梳理出亭与乡里分属于不同的系统,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是为了回避班固十进制的叙述逻辑导致方百里之乡的问题,而据刘昭注的“十里一乡”更正班固的“十亭一乡”,但“亭”与“里”在字形上差别很大,在没有其他版本的支持下就断定《汉书》存在误篡的做法并不可取;[7]二是以刘昭注改定《汉书》,就会导致“十里”分别为“一亭”和“一乡”的冲突,为解决这个矛盾,只好区分班固所述前者为“步里”而后者为“居里”;或者忽略亭与乡的行政性质,亭与乡分别管理十个里,区别不过城乡差别而已。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十里一乡”并无制度规定的佐证和史实的支持,据学者对西北汉简的考察,汉代中等县一乡辖有70个里左右,小县小乡辖有20至40个里左右。[8]另据尹湾汉墓简牍《集簿》的记载,东海郡辖“乡百七十”,辖“里二千五百卅四”,[9]平均每乡约15个里。如此,十个行政里合为一乡的解释是说不通的。
二是“里在亭部”的路径。宫崎市定认为亭和乡都是拥有城郭的聚落,乡与亭并非上下关系,只是左右关系,“十亭一乡”即十个亭中以其中最大的一个“亭”为乡(都亭),其它九个亭则附属之。亭隶属于乡,乡隶属于县。[10]周振鹤从汉代分部监察制度入手,认为“亭部”在理论上是每乡分为十个亭部,以监察位于部内的里,即所谓“十亭一乡”。所谓“十里一亭”,即每十里路设有一亭,一个亭部容纳一个里,在方圆百里的范围内正好可以划分成一百个里,一百个里对应着一百个亭部。由于亭部长宽各十里,因而这个亭又可兼作道路上十里一亭的亭。[11]
“里在亭部”说虽无改字之嫌,却是主观描绘秦汉乡亭里设计图的畅想。在宫崎市定的构思中,亭散布于荒郊田野,每个亭的周围平均簇拥着十个里,但他忘记了任何类型的“乡亭”都不能远离聚落和交通,如何才能形成十个里簇拥一个亭呢。另外,他一方面说亭与乡是左右关系,一方面又说亭隶属于乡,这本身也是矛盾的。周振鹤的解释比宫崎氏前进了一步,他以十平方里对应亭部,每十个亭部合为一乡,从字面上似乎解决了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递进关系,但仔细推敲这个结论依旧站不住。对此,前辈学者已经指出了周振鹤的逻辑错误,即按他的演绎就会出现“万户乡”和“方百里”之乡,一乡的面积和户数相当于一个县,无论如何都与秦汉制度不合。[12]
因此,解决秦汉时期亭的设置及其与乡里之间的关系,还是要在“信古”的前提下去思考,虽然也有学者质疑“十里一亭”的真实性,[13]但《汉书》对乡亭制度的叙述只能从制度本身获得说明,不宜采取轻易否定的态度。笔者认为,前人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关键是“十亭一乡”的说法超出了人们一般的想象空间,即“十里一亭”的“里”若为道里,“十亭一乡”即方圆百里,已与县的面积相当,按平均每县3-4个乡计算,则远远超出“县大率方百里”的制度设计。其实,如果理解了班固何以要在《百官公卿表》特别记录县的面积,上述纠结或许就能获得大体的说明。《百官公卿表》叙西汉官制自三公九卿下至郡守郡尉,一般直录中央与地方的官署、主官的职掌与秩级、诸曹吏员设置及秩级,附带叙及机构沿革及更名情况,唯独在记录县乡机构时具体谈到县的面积。即是说,班固是把乡亭吏员的设置和县面积的构成糅合在一起记录下来的,对县面积的计算以“方百里”为标准,在边长各百里的范围内以“亭”的间距设计“乡”的间距,同时附记乡亭的吏员设置,此即所谓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而这个间距只是一个公约数,不过“大率”而已,实际中,既可以小于这个“十里”,也可以大于这个“十里”,故曰“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在班固的笔下,已经告诫后人不可机械地理解。
那么,这样的“方百里”的标准县是依据制度规定,有其现实基础,还是一种纯粹的理想构思呢?要理解这个问题,恐怕要从秦汉制度是从封国时代发展而来的历史轨迹来思考。秦制行政县确立于商鞅变法,《史记·秦本纪》曰: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14]《六国年表》载其事曰:“初聚小邑”,[15]《商君列传》总其成曰“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16]。文中提到的“聚”“邑”指的都是规模较小的聚落,“聚”一般指自然形成的聚居区,“邑”指经过人为规划的居住区,这些聚和邑是历史形成的,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且,先民选择居住地首先考虑的是就近水源,所以关中河谷平原上星罗棋布的聚落是沿着渭水、汧水、泾水、洛水等水系呈带状分布的,其中较大的聚落演变为国家形态下的都邑、采邑和乡邑,所谓“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17],都邑与采邑、采邑与采邑之间修筑有交通道路。商鞅建立的四十一县就是在这些由交通网络连结而成的聚落群“并诸小乡聚”、“聚小邑”,按“县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组建而成的。由于当时的县治大多密集地坐落在交通线上,所以县与县之间的距离是可以通过各级道路上的标识物来计算的。西周以来,为了军旅通使等需要在交通要道上设有委积和路室,《周礼·地官·遗人》说:“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郑玄注曰:“庐,若今野候,徒有庌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18]春秋战国以后,由于信息传递和文书行政的需要,交通干线上建立了亭、邮、置等不同等级的邮驿机构,这些机构有固定的里程规定,一般是以“十里”为基准的。据吴荣曾先生考证,古代的“邮”必有“亭”,故习惯上也称“邮亭”。[19]所以,县的面积就是以十进制为单位计算的,其标识物就是“亭”。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班固的记述中,不仅“十里一亭”的“里”指的是“里程”,而且“十亭一乡”的“亭”指的也是里程。即在交通干线上,十里设一亭,十亭的距离设一乡。由于这个“乡”是用来规制县与县之间的间距的,所以这个“乡”指的是交通要道经过的大乡,亦即都乡,而非向县域纵深设置的离乡。“十亭一乡”说的是十个亭的距离设置一个都乡,亦即一县治,并非要求县治之间一定要等距离设置十个亭,至于县治与离乡的距离以及离乡与离乡、离乡与邻县离乡之间的距离则根据聚落分布的情况而定,并不会要求等齐划一。当我们把这种制度与秦代关中东西交通大动脉上分布的县邑略加比照,就会发现班固的说法是大体不误的。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标识的“西汉司隶部”各县的位置与今地名的对应关系,以现在的公路里程计算,汉代关中交通干线上分布的县与县之间的距离大致都在100汉里左右。[20]
我们说“十亭一乡”指的是十亭的距离,这是考虑到当时的交通道路存在不同等级。由于主要交通干道肩负着上下文书的运行和重要信息的快速传递,驰道、直道以及担负防御任务的北部边郡的交通沿线“十里一亭”也是可能的,如汉初《行书律》就规定:
十里一邮。南郡江水以南,至
(索)南界,廿里一邮……北地、上、陇西,卅里一邮。[21]
从亭的实际设置距离来说,张俊民根据敦煌悬泉汉简复原了敦煌郡效谷县邮路上各种亭、置、骑置等邮驿机构的位置及大致里程,由效谷县西门亭东至广至县的石靡亭,邮路上的机构设置依次是:西门亭一安民亭一甘泉骑置一××亭一遮要置一××亭一平望骑置一毋穷亭一悬泉置一临泉置一石靡亭,总里程140汉里,亭与亭、亭与置之间的平均间距为14汉里,[22]其中还包括延伸到广至县境内的部分。由此可见,西北邮路上邮驿机构的间距大体是按“十里一亭”设置的,县的面积也完全可以按“十亭一乡”来表示。正因为如此,古人对班固的记载并不怀疑,李昉等在《太平御览》“驰道”目下,引贾山语“秦为驰道,东穷燕齐”的议论,即直录《百官公卿表》的十里一亭,十亭一乡。[23]
交通干线以外的郡县交通则没有必要“十里一亭”,所谓“十亭一乡”不过按标准县的设计图式表示县距而已,并非一个乡拥有十个亭。冨谷至受张家山汉简《行书律》的启发,肯定《汉旧仪》所谓“设十里一亭,亭长,亭候”[24]的“十里”表示的是里程,认为“十里一亭”是关于邮亭设置的规定,[25]这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像。但他在解释“十亭一乡”时,又陷入积亭为乡的传统认识窠臼,认为班固的记述是把有关邮亭的规定与其他有关县、乡等基层行政组织的规定混在了一起,进而推论出“一乡之中平均包含了十个亭”的结论。但他忘了这个平均数是不存在的,因为据《百官公卿表》的记载,西汉末全国“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26]平均每乡4.48个亭;据《续汉书·郡国志》注引《东观书》曰:“永兴元年,乡三千六百八十二,亭万二千四百四十二”,[27]平均每乡3.38个亭。由此可见,用“十亭一乡”机械地理解汉代乡亭的实际配置比例,只能为了凑齐“十亭一乡”的亭数,而置汉代乡亭设置的历史真实于不顾。
由此可见,所谓“十里一亭”是为了解决邮书传递而设计的主要交通沿线邮驿机构的大致间距,“十亭一乡”是以不同的邮驿机构为标识测算出来的县面积,即都乡与都乡的大概距离,而非一个乡一定要平均设置十个亭。这种制度设计源自封国时代的秦国,具体说是在行政县制推广过程中为适应历史形成的聚落分布的现实基础而做出的规制,是秦汉时期真实的制度性存在。
二、邮亭、乡亭与交通级别
据简牍资料揭示,秦汉时期的文书传递或称“以邮行”,或称“以亭行”。两者有何区别,以往一般是从行书的快慢和文书的重要程度加以区分的,没有注意到两者传递路线的级别问题。笔者认为,邮亭与乡亭都具备食宿与传递的功能,区别是邮亭主要设置于京师与郡国、郡国与县邑的主要交通沿线,取道邮亭的文书传递称“以邮行”;兼行邮书职能的乡亭主要设置于郡国辖区中的次级交通道路,取道乡亭的邮书传递称“以亭行”。[28]
邮亭设置于主要交通干线,这在史书中是有迹可循的。如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汝南新息人高获“素善天文,晓遁甲”,时郡境大旱,太守鲍昱屈尊请教致雨良策,高获曰“急罢三部督邮,明府当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文中的“三十里亭”,《谢承后汉书》作“四十里亭”,[29]孰是孰非另当别论,却透露出这类“亭”是以十里为基本单位的信息。况且高获在建言中要求“罢三部督邮”,说明这个“三十里亭”与督邮有关,李贤注引《续汉书》曰:“监属县有三部,每部督邮书掾一人。”[30]桓帝时赵咨拜东海相,道经荥阳,前在敦煌所荐孝廉曹暠时为荥阳令,“迎路谒候,咨不为留。暠送至亭次,望尘不及”。[31]荥阳地处东西交通枢纽,以次设置的“亭”应当就是“邮亭”,故薛宣子薛惠为彭城令时,薛宣从临淮迁任陈留太守途经荥阳,才有“桥梁邮亭不修”[32]的说法。由此可见,当时设置于中原交通大动脉上的亭基本都是“邮亭”,由于邮亭与邮亭之间的间距是按“十里一亭”“廿里一邮”设计的,所以才以里程或亭次称之。
不论是内郡还是边郡,主要交通沿线都有邮亭相连。[33]交通干线之外沟通县与县、县与乡的道路上是否设置邮亭,仅据文献记载不得而知。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剖析尹湾汉简的相关内容作进一步分析。
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集簿》,载东海郡下辖的38个县邑侯国置“邮卅四”。东海郡辖境面积“界东西五百五十一里,南北四百八十八里”,在幅员如此辽阔的辖域内分布38个县级单位和170乡,县与县、县与乡之间应有各种级别的交通网络,可区区34个“邮”若平均分布于纵横交错的交通路线上,如何能满足文书传递的需要呢?故笔者怀疑这些“邮”应当设置于郡内重要的交通道路上,因为在《东海郡吏员簿》记录的县邑侯国的吏员编制中,只有6个县邑设置了“邮佐”,分别是:郯县2、临沂2、费县2、下邳2、利成1、兰旗1。按照前文的推测,这几个设邮佐的县邑应当位于当时的主要交通干线上。具体来说,郯县地处郡境中部,是东海郡郡治所在地;临沂在今临沂市兰山区北境,沿沂水西岸可达费县;费县位于郯县西北与泰山郡交界处,是郡都尉治所;利成在今山东临沭东,西接临沂,东与朐县(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相连;下邳在今邳州市南古邳镇,与楚国、临淮郡接壤。由以上设置邮佐的城邑为支点大体可以构成北起临沂南至下邳的纵向交通,东起利成经临沂西至费县的横向交通。兰旗侯国地望不详,郑威认为当即雍正《山东通志》所载之“兰城”,城址位于今枣庄市台儿庄区兰城店乡。[34]若此,郯县至兰旗构成东海郡中西部的另一条横向交通。至此,由以上6个设邮佐的县邑就联成东海郡一纵二横的交通干线,即:
一纵自南而北:下邳一良成一郯县一临沂
一横自东而西:朐县一赣榆一利成一临沂一费县
二横自东而西:……郯县一兰旗
这三条道路的总里程如果暂时不计朐县至利成段,按现在的公路里程计算约为328.6公里,约合792汉里,[35]按“十里一邮”需置79个邮,按“廿里一邮”需置39.6个邮,按“卅里一邮”需置26.4个邮。由此来看,东海郡置“邮卅四”是符合制度规定的。东海郡地处帝国东境,虽然属于边郡,但当时并无来自海上的威胁,所以邮佐的设置主要分布于纵向交通线以东,这与郡政主要面向帝国腹地也是相应的。另外,海西(今江苏灌南东南)当时是东海郡最大的一个县,吏员多达107人,比郯县的95人还要多,因此,从海西至郯县应有一条横向交通,即从海西经曲阳、厚丘,北上今东海县西至郯县,从而与郯县至兰旗路相连。但从海西到郯县以及从朐县到利成所经过的县邑并没有设置邮佐,[36]这些路线以及其余县邑与郯县之间以及县邑之间的文书传递,或许只能通过乡亭系统“以亭传”。对此,我们缺少直接的证据,只能通过比照东海郡所辖县邑设置乡亭的多少做一些推测性的工作。根据东海郡县邑侯国乡、亭吏员配置数量可知,海西、朐县地处沿海,海西经厚丘至郯县,赣榆经朐县至利成作为东海郡东部的两条横向交通,虽然由于军事价值不大没有邮亭的设置,但这些城邑附近及道路沿线乡亭设置的数量却很多,乡、亭比分别为:海西14:54、朐县7:47、厚丘9:36。另外,交通干道之外郡内县邑之间由于文书传递的需要,同样设置了许多乡亭。如郡境北部的南城侯国3乡19亭,利成东北的况其5乡32亭,今江苏新沂市南的建陵侯国1乡6亭,今江苏沭阳东的曲阳1乡5亭;郡西部的缯县4乡23亭。这些县邑因为远离郡治郯县,又不在主要邮路沿线,所以也设置了许多乡亭。
当然,我们的结论不能仅仅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之上,对于邮亭与乡亭设置地点的区分还可以从湖南苏仙桥晋简获得间接证明。苏仙桥遗址J10古井出土的西晋木简中涉及邮、驿、亭关系的简文有如下记录:
1-4
度亭西到故长连邮廿五里废无居人
1-6 长连邮西到深浦亭十五里不在正路依己卯诏书省
1-55 都邮北到故佳邮十里废无居人
1-74 挛德亭到故佳邮六里废无居人今置迷桥驿
2-359 洛泉邮西北到松亭十五里不在正路依己卯诏书省
2-374 谷驿南到故松泊邮十五里废无居人
2-386 故谷亭一所废无居人
根据这批木简中的纪年简可知,简文内容属于晋惠帝时期桂阳郡郡府文书档案。[37]据学者研究,魏晋制度直接承袭汉制而来,邮亭驿系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存在。[38]如此,我们是可以据此反推秦汉亭制的。苏仙桥晋简提到了三个废弃的邮:长连邮、佳邮、松泊邮,所以才称“故××邮”,废弃的原因不明,其中,佳邮根据需要另置“迷桥驿”。有两个亭由于“不在正路”而废弃,分别是“ 度亭”和“松亭”。与我们的论题相关的是
度亭”和“松亭”。与我们的论题相关的是 度亭、松亭应当是次级交通路线上的乡亭,因此才“不在正路”,设置的路线属于通向郡域其他县邑的郡级交通,这与我们在前文推测的东海郡从海西到郯县、从朐县到利成以及从郯县到其他县邑的文书传递要通过乡亭“以亭行”的结论是基本吻合的。
度亭、松亭应当是次级交通路线上的乡亭,因此才“不在正路”,设置的路线属于通向郡域其他县邑的郡级交通,这与我们在前文推测的东海郡从海西到郯县、从朐县到利成以及从郯县到其他县邑的文书传递要通过乡亭“以亭行”的结论是基本吻合的。
综上说明,乡亭的设置原则一是不能远离聚落,二是不能脱离交通。城邑内的亭依据其不同功能各有名号,城邑外的亭大体分为乡亭和邮亭。邮亭和乡亭都具有文书传递和提供食宿的功能,区别是邮亭主要设置于京师与郡国、郡国与县邑的主要交通沿线,乡亭主要设置于郡国辖区中的次级交通道路。
三、亭部与自然聚落“丘”
一般说来,兼具治安与行书功能的乡亭是以各种级别的道路为轴心设置于聚落附近的,即使远离聚落的乡亭似乎也不可能脱离交通而设置于田野或荒原。乡亭既然以索捕盗贼、调查案情为主要职责,从其创制伊始就当划定一定范围的责任区。比如长安、洛阳城内的治安亭,辖区是按街道划分的,所谓“街一亭”是也。乡亭同样需要划定其巡徼的范围,如果说“十里一亭”的“里”可以按方圆计,则乡亭的责任范围或许大略如此。
城邑之外的乡亭是否有固定的辖区,以往我们并不知晓,按史书的记载有“亭部”的说法。“亭部”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汉元帝时期,但并不意味乡亭的辖区此时才开始划定,对此,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线索。比如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收录的“群盗”爰书就记录了某亭长与求盗逮捕群盗的经过,大意是说某校长(即亭长)甲与求盗乙、丙“徼循到某山”时,发现群盗人丁和戊藏匿山中,于是斩首戊,捕获丁。[39]爰书提到的“徼循”,应即亭长按制在辖区中巡行。这种责任区在简牍资料中也称“部中”,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收录的一件案例记载,高祖六年六月,淮阳郡新郪狱史“武”出备盗贼至公粱亭失踪20余天,而新郪令“信”不予“穷讯”,公粱亭长“丙”坐罪无“毄(系)牒”。淮阳守“偃”疑有奸诈,举劾覆审。与“武”同行的新郪髳长“苍”坦白:“故为新郪信舍人,信谓苍:武不善,杀去之。苍即与求盗大夫布、舍人簪裊余共杀武于校长丙部中。丙与发弩荷(苛)捕苍,苍曰为信杀,即纵苍,它如劾。”[40]供词中提到的公粱亭“校长丙部中”,文献简称“亭部”。也就是说,乡亭有固定的管辖区是与亭的治安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并非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层级监察制度的形成才划定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耕垦的需要,百姓会不断从城邑沿着交通道路向四周扩散,在远离城邑的地方聚居,形成新的聚落,因此,原本出于邮驿的需要设置在荒凉地带的邮亭、乡亭附近也会逐渐形成新的聚落。如:章帝元和二年九月诏:“凤皇、黄龙所见亭部,无出二年租赋。”[41]安帝延光三年二月诏:“济南上言,凤皇集台县丞霍收舍树上……凤皇所过亭部,无出今年田租。”[42]以上记载说明亭部之中有民户居住,只是这些错落于亭部的聚落名称以及这些聚落的隶属关系还不清楚。另外,东汉时期列侯封爵中有“亭侯”之称,亭侯作为列侯的一等,据研究始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43]封户从100户到1500户不等。所谓亭侯即以亭为名,将亭部内居住的民户作为封侯所食封户,如《续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记》称:“曹腾封费亭侯,县有费亭是也。”[44]至于亭部内居民的管理方式,从文献记载而言不得而知。按秦汉制度和一般性常识,聚落的居住区一般是称“里”的,城邑如此,乡村也是如此,即便是汉初地处汉与南越缓冲地带的长沙国南部,原本依山傍水自然形成的聚落被纳入国家行政管辖后也同样设乡置里。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驻军图”就用红圈标示了42个里名,户数参差不齐,多者百余户,少者十几户。[45]然时过境迁,东汉中期以后,在同属长沙郡的临湘县乡里行政系统之外,又出现了“丘”的概念,比如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既能见到乡统里的管理体系,又能见到“亭”辖“丘”的统辖关系。诸如:
1.木牍CWJI③:71-26云:●案:都乡漻阳里大男马胡、南乡不处里区冯,皆坐。
2.木两行CWJI①:85云:辞:本县奇乡民,前流客,占属临湘南乡乐成里。
3.木两行CWJI①:93:皆曰:县民,占有庐舍长赖亭部庐蒲丘。
4.木两行CWJI③:292-6:详弟终、终弟护;晨与父宫、同产兄夜、夜弟疑、疑女弟捐;戆与母妾、同产弟强;除与妻委、子女婴俱居自有庐舍伦亭部。尼、晨、除,汉丘;戆,上辱丘。
5. 木两行CWJI③:172:姓名如牒。普,都乡三门亭部。董、旦,桑乡广亭部。董与父老、母何、同产兄辅、弟农俱居。旦父母皆前物故,往不处年,嫁为良妻,与良父平、母真俱□□□庐舍。
6.木两行CWJI③:325-4-26:有庐舍庾亭部,以绩织为事。
7.木两行CWJI③:264-34:辞皆曰:县民,宠与父武、母臧及
、汉妻姃等俱居,各有庐舍监亭部。宠,堤下;汉、抚,松田丘。相比近,皆各以田作为事。[46]
由于目前只公布了这批简牍中的极少部分,亭与丘的关系暂时还不是十分清楚,但以下几点还是明确的:
一、临湘县境内的基层居民编制体制存在乡一里、亭一丘的并存关系。乡里关系如例1的漻阳里隶属都乡,例2的乐成里隶属南乡;亭丘关系如例3的长赖亭部的庐蒲丘,例4的伦亭部的汉丘、上辱丘,例7的监亭部的堤下丘、松田丘。这些“丘”只标识了居住地点,没有明确行政隶属关系,但却称“丘”而不称“里”,说明这些“丘”不是按乡里行政关系编组的,而是单纯的地域单位名称。
二、亭部划定于诸乡的乡域之内,但不存在乡统亭的行政隶属关系。黄朴华先生认为当时不仅有乡辖里的居地划分,同时也有乡统亭、亭辖丘的区域划分。[47]实际上,“乡统亭”在已公布的简牍文书中还见不到直接的证据,只有例5的“姓名如牒。普,都乡三门亭部。董、旦,桑乡广亭部”[48]等提法,从字面来说指的是涉案人定居的地点,即某人所处的“亭部”位于某乡的乡域之中。按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乡、亭都是郡县的派出机构,在制度上分属于不同的行政系统,由于亭附丽于乡里而设,乡部与亭部之间必然存在业务往来,但两者在行政级别上属于平行关系,而不是上下统属关系。进一步说,既然“丘”不在乡里编制之内,那就只能另有一套管理体系,如果说由于聚落向乡野扩散进而带动管理方式的转变,也只能是乡统里、亭统丘的双轨制。
三、亭部居民的住宅称“庐舍”,而不称“里舍”。“庐舍”在秦汉文献中多指邑里之外的住处,与“里舍”“里宅”的区别在于它的临时性和简易性,林尹注《周礼·天官·宫伯》“大丧,则授庐舍”句,引贾疏云:“谓于中门之外东墙下倚木为庐,但以草夹障,不以泥塗之也。舍,堊室也。”[49]何为“堊室”?刘熙《释名》曰:“堊:亚也,次也。先泥之,次以白灰饰之也。”[50]丘民的房舍称“庐舍”,说明亭部的丘无非都是一些新形成的聚落,当即哀帝时贾让在“奏治河三策”中所谓“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51]这些“丘”虽然地处某某乡域,但与乡部路途较远,由所在亭部兼理或者是顺理成章的事,也就是说,“丘”的出现表明国家对乡村控制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亭辖丘或许处于由传统的乡里体制向乡辖丘转变的过渡阶段。
用“丘”指称邑外的聚落,文献无载,走马楼三国吴简最早出现乡辖丘的对应关系,见于长沙郡临湘侯国的各种簿籍文书。从制度史的角度来说,秦汉时期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是乡里制,吴简中出现的“丘”属性如何,与乡里又是什么关系?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上述问题学界曾展开旷日持久的讨论,对其主要观点,侯旭东做了很好的总结。[52]从文献记载来说,秦汉指称自然形成的聚落一般是称“聚”或“聚落”的,今长沙地区出土的简牍何以称“丘”,用“丘”指称自然聚落是长沙郡一地的称谓习惯,还是当时的普遍用法,是一个颇为费解的问题。陈絜曾讨论过战国葛陵楚简的“丘”,认为简文涉及的18个“某丘”“某某丘”都是具体的聚落名称,如“桑丘”“上桑丘”等,而不是所谓的山丘或丘陵。[53]如果此说成立,是否楚地以“丘”称谓自然聚落是当地的一种称谓习惯呢?这让我们联想到东汉刘熙对“丘”的解释。刘熙在《释名》中注《周礼》所载都鄙井田之法的“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的“丘”,曰:“丘,聚也。”[54]刘熙以汉代观念释“四邑为丘”[55]的丘为“聚”,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刘熙又名刘熹,北海人,汉献帝建安年间南下避乱,久居交州,[56]所著《释名》是一部从语音学的角度推求字义的著述,《颜氏家训》所谓:“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57]即是说,当地对那些不再设里的自然聚落在命名上是按本地的发音习惯称为“××丘”的,而长沙五一广场附近发现的简牍又都属于长沙郡内的往来文书,采用当地特有的概念“丘”也在情理之中。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的丘,大都见于各种案件的审讯记录,在官方供诉和嫌疑人自诉时记录下其家庭住址在“××亭部”的“××丘”。问题是,这些涉案人在供诉其居住的“丘”时,何以不称“××乡一××丘”而称“××亭部一××丘”?这恐怕要从“丘”的形成过程来解释。众所周知,春秋战国以来不断掀起筑城高潮,邑居成为秦汉时期的主要居住形态,当时的郡国城、县邑城大多建有城郭,离乡离邑虽然没有城郭,或者存在墙垣一类的围护。同时,远离城邑的地方也不断形成新的自然聚落,这些聚落一般是开放式的,比如河南内黄三杨庄遗址的聚落周围至今也沒有发现围墙一类的痕迹。[58]广大乡村自然聚落的形成,总是要沿着交通道路向两侧拓展,从几户十几户而“渐成聚邑”。正如前文所说,邮亭、乡亭都设置于各级交通沿线及其附近,各有相对固定的辖域,而这些新的聚落“丘”就星罗棋布于亭部之中。这些“丘”大多远离乡部,由乡部直接管理存在空间上的困难。以往,出于对农民的生产过程实施监督以及农田水利规划管理的需要,县廷是选派田啬夫、田佐分部负责的,秦及汉初简牍一般称“田部”。田部废除后,县廷选派临时性的“劝农掾”专司农事活动。劝农掾职在监察,兼行劝课农桑之任。随着亭部之中自然聚落的不断形成,继续采用乡里体制困难重重,或许才转而由 “亭部”兼理部内的“丘”。
做出这样的推测也并非毫无根据,理由就是“劝农掾”往往由负责乡亭、邮亭业务的廷掾充任。如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的二件封匣分别是“东部劝农邮亭掾周安言事”和“左部劝农邮亭掾夏详言事”,[59]时间分属于汉灵帝光和六年和中平三年。此外,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木两行CWJI②:124A面还有“东部劝农贼捕掾”的提法,其文曰:
永初元年正月癸酉朔廿日壬辰,东部劝农贼捕掾迁、游徼尚、驷望亭长范叩头死罪敢言之。廷书曰:言男子吴辅斗伤弟妻爢,亡。逐捕有书。辅以微辦(辩)贼伤爢,所犯无[60]
由此可见,劝农掾或兼行邮亭事或兼行贼捕事,督导农事活动都是和亭部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充分说明“丘”是由亭部分管的。另外,简文中的“驷望亭”,依东牌楼封匣“周安言事”的落款属于邮亭。[61]说明“邮亭”也要分部兼行盗贼事,乡亭、邮亭已经从单一性质的治安、行书机构逐渐演变为合民事、治安、行书为一体的组织。
丘的形成是一个自然过程,在和平年代离不开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出台。按秦汉制度规定,山林草田归国家所有,在人们的观念中“地有草者,尽曰官田”,[62]农民垦荒种地要通过“占垦”的手续才属合法。就现有法律资料来说,此制源自战国时期的国家授田制,如里耶秦简中就保存了两份“谒垦草田”的法律爰书:
卅三年六月庚子朔丁巳,[田]守武爰书:高里士五吾武自言:“谒垦草田六亩,武门外,能□籍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自强东路759号交通运输大厦2-2403号
电话:029-81616443 邮箱:qwyjs221@163.com 邮编:71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