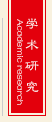從道德正義到政治正義 ——從張家山漢簡《蓋廬》看先秦時代兵家思想的一個側面
发布人:中国秦文研究会秦文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5-06-20 12:01 点击率:216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王启发
1983年湖北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墓所發現的竹簡《蓋廬》,被學界視爲與早已失傳的先秦兵家之一伍子胥的著述有關的文獻再現。至今,學界也有一些多角度的相關研究。
通覽《蓋廬》,筆者認爲其第八章、第九章的內容很值得關注,這兩章分別就蓋廬(闔廬)所問的“吾欲殺其害民者,若何”和“以德攻何如”,在申胥(伍子胥)的回答中列出了多項必須加以“攻之”的行爲對象,而這些行爲對象都是有違當時通行道德的事情,涉及到日常生活、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諸多方面。其中體現出一種正義原則和標準的確定問題,這個標準首先是道德層面的判斷,進而延伸到政治層面的“救民之道”和“救亂之道”的判斷。
古來兵刑不分,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大用甲兵,小用鞭撲,却有著一定的正義原則和標準,這就是從道德正義到政治正義的原則和標準。《蓋廬》第八章、第九章中的所謂“攻”,也就是針對各種不道德行爲所采取的多種打擊和制裁手段的體現。本文試圖通過對《蓋廬》第八章、第九章內容的解讀和分析,從而引出對于先秦兵家思想中有關正義的原則及標準作對比性考察,以此來認識先秦時代兵家思想的一個側面,以及其與諸子百家思想上在道德正義和政治正義原則與標準方面,相互融通和异曲同工的共通性特點。
人類社會首先是道德社會。道德成爲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本標準。道德正義則成爲人類法制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歷史上,無論是思想家,還是政治家,都在如何從道德正義走向政治正義的道路上跋涉,儘管有時候會出現道德形而上意義上的思想背離和目標背離,但是道德理想主義和政治理想主義的天然使命,促使歷史上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不能不去面對道德與政治相統一的問題。有什麽樣的道德,就有什麽樣的政治。這也是中國古代兵家思想中的一個側面。
何谓“道德正义”?當人們講到“道”、“德”、“義”、“禮”、“信”等傳統的德目時,就已經出現了道德正義的價值判斷,換言之,以“有道”、“有德”、“有義”、“有禮”、“有信”來表述的話,所代表的道德正義就更加明確了,相應地,“無道”、“無德”、“無義”、“無禮”、“無信”就是不道德的非正義了。其他的還有不仁、不義、不慈、不孝、不忠、不信、不敬、不悌、非仁、非義、非禮等等。那么,只要是對道德的否定(不、非)和缺失(無),就是道德正義的反面即非正義。
一 張家山漢簡《蓋廬》第八章、第九章內容解析
我的考察就先從對《蓋廬》的第八章和第九章內容的解析開始[1],幷且結合《蓋廬》第一章的內容進行比較,來討論和說明這三方面內容的聯繫性和在所謂家族倫理、社會倫理、政治倫理方面所體現的正義原則問題。
(一)《蓋廬》第八章的内容解析
《蓋廬》第八章開始所記蓋廬曰:“天之生民,無有恒親[2],相利則吉,相害則滅。吾欲殺其害民者,若何?”這裏,作爲執政者的蓋廬[3],關注到其統治下的民衆的社會生活,意識到民衆生活的好壞取决于民衆相互間的利害關係,于是他想要通過殺伐[4]的手段來爲民除害,以保障民衆的社會生活安定和諧。這當然是一個關乎政治的目的的問題,也就是說以“欲殺其害民者”作爲執政的目標之一的。然而,關鍵在于應該以什麽標準來判定害民者,所以就向臣下申胥(伍子胥)提出詢問。
有關“天之生民”[5]的思考,墨子有云:“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是以分國建諸侯。……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墨子·尚同下》)荀子有云:“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荀子·大略》[6])这一段似乎正可以做蓋廬發出上述問題的一個很好的注脚。[7]
有關“相利則吉,相害則滅”,与《墨子·法儀》中的说法有所联系。“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这与盖庐所言的意思也相吻合。
說到“相利”,墨子有“兼相愛,交相利”的說法,幷且以商湯、周文時代的政治爲例來證明。《墨子·非命上》有云:“古者湯封于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昔者文王封于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說到“相害”,墨子也有言說,《墨子·魯問》有云:“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交相鈎,交相强,猶若相害也。”在墨子的法天思想中也有相關表述,《墨子·法儀》有云:“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
針對蓋廬的提問,申胥(伍子胥)有關“救民之道”的回答,便充滿了一系列的道德標準和判斷,也爲後人展現了春秋時代的通行道德。
申胥曰:“貴而毋義,富而不施者,攻之。不孝父兄,不敬長傁者,攻之。不茲(慈)穉弟(悌),不入倫雉者,攻之。商販賈市,約賈(價)強買不已者,攻之。居里不正直,強而不聽□正,出入不請者,攻之。公耳公孫,與耳□門,暴敖(驁)不鄰者,攻之。為吏不直,狂(枉)法式,留難必得者,攻之。不喜田作,出入甚客者,攻之。常以奪人,眾以無親,喜反人者,攻之。此十者,救民道也。”
對于以上“申胥曰”的內容,我們不妨參考《張家山漢簡》注釋者的注釋,以及連劭名《張家山漢簡<蓋廬>考述》一文中的考述[8],简要归纳性地来做一些進一步的解讀和分析。
(1)“貴而毋義,富而不施者”。這是指作爲富貴人家而“不義不施”的不道德行爲;相關的道德要求則是貴而有義,富而好(樂)施。
從社會階層意義上講,何爲“富貴”呢?孔夫子曾言:“吾貧且賤。”那麽,貴富之家當出于官吏和商人。貴賤在于身份地位的高下,貧富則是財富擁有量的多少。《易傳》中有言:“崇髙莫大乎富貴。”
說到“富貴”,墨子也有相關的話語。他說:“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墨子·尚賢上》)“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顔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同上)[9]
所謂“毋義”就是“無義”,如《尚書·周書·康誥》有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不施”,就是無所施予。如《左傳·昭公十三年》所記叔向有言:“不藏賄,不従欲,施捨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無施于民,無援于外……何以冀國?”在這個意義上,都應該是有地位勢力者的德行表現。對富貴者的道德要求如何,應該是社會進步的一個尺度。
還可以參考的是,《論語·學而》有云:“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傳·定公十五年》记载:“史鰍曰:‘富而能臣,必免于難。……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10]《左傳·昭公元年》有云:“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此外,從國家政治意義上來說,國家富足而不見施于下民,也是不好的,如《管子·法法》所說:“足而不施,殆。”唐房玄齡注:“足而不施,怨疾必生。”
(2)“不孝父兄,不敬長傁者”,“不茲(慈)穉弟,不入倫雉者”。這兩條的内容相关,對前一條中的“傁”,《漢簡》整理注釋者稱:“《方言》六,‘長老也。’與叟字通。”對後一條,《漢簡》整理注釋者認爲,“稚”同“稚”,“雉”讀作“第”。
這裏指的是不遵守家族倫理,破壞家族秩序、違背人倫道德的行爲。《左傳·隱公三年》有石碏之言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爲“順德”,以“少陵長,遠間親”爲逆德。而《尚書·康誥》有雲:“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由此[11]可知,对不孝不友不慈不悌的行为,在刑罚上有所惩戒,作为一个传统早在西周文王武王时代就是如此了。在后来的历史上,“不孝不睦”更被列为所谓“十恶”重罪当中。
(3)“商販賈市,約賈(價)強買不已者”。對這裏的“約”字,《漢簡》整理注釋者稱引《淮南子·主術》高誘注:“少也。”那麽,這就是指壓低商品價格,破壞商品買賣市場秩序的行爲。
我們知道,《周禮·天官冢宰》中的“大宰之職”就有“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而且《周禮·地官司徒》中還有相應的職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度量、禁令……以量度成賈而徵儥……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對“以量度成賈(價)而徵儥”,鄭玄注云:“徵,召也。儥,買也。物有定賈(價)則買者來也。”此外,在《周禮·地官司徒》中,還有“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還有“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還有“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還有“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春秋時代各諸侯國,特別是吳國。是否有如上述《周禮》中那樣完備的商品市場管理制度無法確定。但是有一定的市場價格規範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違反了這個規範,就會有所懲罰,就是《蓋廬》此條給我們的認識。
(4)“居里不正直,强而不聽□正,出入不請者”。这里的“□”的缺字,《漢簡》整理注釋者認爲當爲“里”字。里正就是里长。而王貴元則認爲可以看出是“灋”字,與後面“狂(枉)灋式”中的“灋”字寫法相同,且稱“灋正”就是禮法規矩的意思;幷引述《荀子·性惡》“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灋正”,還有《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高柴,……字子羔,……爲人篤孝而有灋正”兩段來證明。邵鴻亦從王說。
這條是指在鄉裏的居處生活中,蛮横而不遵从里正指挥(或礼法规矩),不做請示就隨意出入的人。
“正直”是一種爲人的品德。《尚書·洪范》有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潜,剛克;高明,柔克。”對此“正直”,漢孔安國《尚書傳》解釋說:“能正人之曲直。”《詩經·小雅·穀風之什·小明》中也有兩處說到“正直”:“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韓詩外傳》卷七第二十一章有云:“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那麽,《蓋廬》此條所講的“不正直”也就是指自私、不公正、不講道理的行爲,“强而不聽”、“出入不請”也同樣屬于不講道理、不守規矩的行爲。
(5)“公耳公孫,與耳□門,暴敖(驁)不鄰者”。“耳”,《汉简》注释者称“即耳孙”,并引述《汉书·惠帝纪》“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句下顔師古注引李斐說爲曾孫。
其實,顔師古注引述有諸家說法。其中,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逺,但耳聞之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
顔師古本人則說:“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䪘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
“鄰”,《漢簡》注釋者引述《左傳·昭公十二年》“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一句的杜佑注說“鄰,猶親也”。
此外,《周禮·遂人》有“五家爲鄰,五鄰爲裏,四裏爲酂”之說。鄭玄引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异制,故五家爲鄰。”
這一條,正如連劭名所解釋的那樣,就是指貴族豪門子弟橫行鄉里的行爲。
(6)“爲吏不直,狂(枉)灋式,留難必得者”。這裏就是指爲官的不公正、貪贓枉法、敲詐勒索的行爲。
這裏的“不直”,如連劭名解說的那樣,秦時已經是一種法律術語。《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罪當重而端輕之,當輕而端重之,是謂‘不直’。”
“狂(枉)灋式”,就是枉法的意思。就“直”和“枉”的關係,《論語·爲政》有言:“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留難”的第一種意思,是指顛沛流連之艱難的狀况,漢焦贛《易林》卷一《屯之涣》有云:“震慄恐懼,多所畏惡,行道留難,不可以涉。”同书卷二《觀之震》有云:“盤紆九回,行道留難,止須千丘,乃睹所歡。”同书卷二《頤之困》有云:“逺視目盼,臨深苦眩,不離越都,旅人留難。”
“留難”的第二種意思,是指無理阻止,故意刁難、挑剔的態度或行爲,漢桓寬《鹽鐵論·本議》:“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爲市。”。這裏應該是後者,連劭名也持此說。那麽“留難必得”,也就是敲詐勒索、從中牟利的意思。
《蓋廬》這一句正面的意思,《孔子家語·辨政》中所記孔子的一段話似乎全都包括了:“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亷,廉平之守,不可改也。”
(7)“不喜田作,出入甚客”。 “客”,《漢簡》整理注釋者稱“疑讀爲‘路’”。而連劭名稱讀爲“格”,幷引《史記·李斯列傳》“而嚴家無格虜者”一句的《索隱》所云“格,强扞也”來說明。這裏姑從連氏之說。
這一條,確實和連氏所引述的《睡虎地秦簡·封軫式》中的“丙,甲臣,不田作”,還有連氏所引述的《六韜·上賢》中的“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法曆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在內容上是很相近的。反映了所關注的是相同的行爲。
我們知道,《周禮·遂人》有云:“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作爲農業社會,田作耕種稼穡之事是主業。《呂氏春秋·上農》有云:“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朴,朴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産復,其産復則重徙,重徙則死處而無二慮。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産約,其産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可見,這裏所講的意思和《蓋廬》所關注的問題也是一樣的。那麽,《蓋廬》此條,指就是不事田作,游手好閑,出入强悍,無事生非的行爲。
(8)“常以奪人,眾以無親,喜反人者”。這一條,指的是經常以强搶、强取損害他人利益[12],衆叛親離,喜與他人作對的行爲。而這些行爲,顯然與孔子所講的“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論語·學而》)的行爲品德背道而馳。也與墨子所主張的“兼相愛,交相利”的行爲品德相違背。
(9)“此十者,救民道也。”《蓋廬》第八章中,申胥在列舉了每一種不道德行爲之後,都發出“攻之”的决斷,幷在最後說:“此十者,救民道也。”細緻數來,申胥只列出了九種應該“攻之”的行爲對象,這個“十”字,或是“九”字之誤,或是如邵鴻所言,抄寫脫漏了一句。還有如邵鴻所說,“救民道也”的“民”後脫一“之”字。
《蓋廬》通篇九章3000多字,出現有50個“攻”字,多數是從兵家軍事戰略戰術所講的“攻擊”。而這裏的“攻”字意思有所不同,應該是指對不道德行爲施行懲戒、處罰的意思。[13]
(二)《蓋廬》第九章的內容解析
如果說,《蓋廬》第八章諸條所顯示的只是在一國之內對官吏的職業道德和民衆的日常道德的約束的話,那麽,第九章則是關涉到國與國之間關係的道德判斷了,所以《蓋廬》第九章講的則是國家政治層面的“德”與“不德”和以“有德攻無德”的問題。而且,第八章是“救民”之道,第九章是“救乱” 之道。
蓋廬曰“以德【攻何如】?”
【申胥曰】:“□(以)德攻者:其毋德者,自置為君,自立為王者,攻之。暴而無親,貪而不仁者,攻之。賦斂重,強奪人者,攻之。刑正(政)危,使民苛者,攻之。緩令而急徵,使務勝者,攻之。□(外)有虎狼之心,內有盜賊之智者,攻之。暴亂毋親而喜相詿者,攻之。眾勞卒罷,慮眾患多者,攻之。中空守疏而無親□□者,攻之。群臣申,三日用暴兵者,攻之。地大而無守備,城眾而無合者,攻之。國□室毋度,名其臺榭,重其正(征)賦者,攻之。國大而德衰,天旱【而】數饑者,攻之。此十者,救亂之道也。”
《蓋廬》第九章中,蓋廬提出的问题是“以德【攻何如】”,而从后面申胥回答的“(以)德攻者”的内容来看,这里的“攻”比第八章的程度要重,有讨伐、攻伐的意思。我们结合当时春秋时代的一些政治历史背景而具体解析如下。
(1)“其毋德者,自置為君,自立為王者,攻之。”這一條很清楚,就是針對當時諸侯國內部政治上經常出現的攻襲、弑殺在位君主或當立爲君主者而自立,甚至是“自立爲王”的現象。而其重點又在于“其毋德者”的這一道德判斷上。
《墨子·三辯》中講到:“湯放桀于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修《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
這裏提到商湯、周武“環天下自立以爲王”的情况,然而在當時湯武都是人們心目中的政治上的有德者。那麽,作爲一種從道德判斷到政治判斷的原則就是,“有德者得在其位,無德者不得在其位”;而《蓋廬》中所要采取的現實態度就是“以有德攻無德”。
有關春秋時期政治史上的“自置為君,自立為王”的現象,史書上有所記載。
第一,《史記·齊太公世家》中記載了分別發生在春秋時期的齊國和魯國的“自立爲君”的事情。
(齊)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
(齊)厘公九年,魯隠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隠公而自立為君。
第二,《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載,春秋十二諸侯國當中的宋國所發生的幾次“自立爲君”,甚至“自立爲王”的事情有:
(宋成公)十七年[14],成公卒[15],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16],是為昭公。
(宋昭公)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17],乃助之施於國[18],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湏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19]
(宋景公)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20]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褍秦,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
(宋)昭公四十七年卒[21],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八年卒[22],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23]
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接著上面而記述了宋國君偃在自立爲王之後發生的各種事情說:“(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滛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輙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24]”
第三,《史記·鄭世家》記述了發生在鄭國兩次“自立爲君”未遂的事情。
(郑)釐公五年[25],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嵗,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産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
第四,《史記·楚世家》記載有楚國君熊通“自立爲王”的事情:
(熊眴)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26],是為楚武王。[27]
有關楚武王自立的過程,司馬遷記述說:
(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聼,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28],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
第五,《史記·楚世家》還記述了楚公子白公勝“自立爲王”的事情。
(楚)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於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刼恵王,置之髙府,欲弑之。恵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恵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恵王乃復位。
第六,《史記·管蔡世家》有記載:
(蔡莊侯)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
(蔡景侯)四十九年,景侯為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
(蔡)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弑其王郟敖而自立,為靈王。……(靈侯)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于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棄疾為蔡公。
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為平侯。
(蔡)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為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
此外,《史記·衛世家》和《鄭世家》也皆有記載;“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
第七,《史記·管蔡世家》中所附“曹叔世家”記載了曹國發生的幾次“弑君代立”的事情:
(曹)幽伯(彊)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
(曹惠伯)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
(曹)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為隱公。
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為靖公。
《史記·陳杞世家》还有記載說:“(杞)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弑隱公自立,是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閼路弑湣公代立,是為哀公。”
第八,在《史記·楚世家》中,還記述了發生在吳王闔廬弟弟夫概身上的自立爲王事件。
(楚昭王)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29]。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
其實,除了上述發生在闔廬弟弟夫概身上的事情之外,還有發生在闔廬本人與吳王僚之間的,具有“弑君代立”性質的事件。《史記·吳太伯世家》的記載如下:
二十五年[30],王壽夢卒。
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夀夢欲立之,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