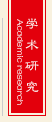秦汉时期民众的法律意识
发布人:中国秦文研究会秦文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5-06-18 21:53 点击率:2468
邬文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虽然典籍中少有关于秦汉时期民众法律意识的直接描述,但史实表明,秦汉统治者重视对民众的法律教育,因而民众对法律知识有着广泛的了解,已经形成了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意识,并懂得利用法律手段、诉诸官府来解决纠纷,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民众也有较强的法律参与意识,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身对法律的诉求和执法官吏的期待。
一、法律意识
秦国商鞅变法,即通过“悬法象魏”、“徙木立信”等手段向天下吏民公布法律、进行法律教育,确立法律的权威性,使得法律意识日渐深入人心。敬畏法律、遵守法律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或生活常态。商鞅被拒于客舍之外的故事即表明了这一点。《史记·商君列传》载:“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
出土秦代简牍中有一类是《日书》,即日者选择时日、占断吉凶的实用手册,主要流行于民间社会,因此它反映了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的实态。通常《日书》占卜的内容主要是生老病死、衣食居行、婚姻嫁娶等,但在周家台三十号秦墓出土的秦简《日书》“二十八宿”占中则出现了占狱讼的内容,兹略举数例如下:
角:斗乘角,门有客,所言者急事也。[占]狱讼,不吉;约结,成;逐盗、追亡人,得;占病者,已;占行者,未发;占来者,未至;占[市旅]者,不吉;占物,黄、白;[占]战斗,不合。
[氐:斗乘]氐,门有客,所言者忧病事也。占狱讼,不解;占约结,相氐乱也;占逐盗、追亡人,得之;占病者,笃;[占行]者,不发;占来者,亟至;占市旅,不吉;占物,青、黄;占战斗,不吉。
[房:斗乘]房,门有客,所言者家室事,人中子也,多昆弟。占狱讼,解;占约结,成;占逐盗、追亡人,得之;占病,少[可;占行者,![]() ;占来]者,未至;占市旅,吉;占物,白;占战斗,不合。
;占来]者,未至;占市旅,吉;占物,白;占战斗,不合。
[尾:斗]乘尾,门有客,所言者吉事也。占狱讼,胜;占约结,成;占逐盗、追亡人,得之;占病者,已;占行者,己发;占来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青、黄;占战斗,胜,不合。
箕:斗乘箕,门有客,所言者急,善事成,不善不成。占狱讼,急,后解;占约结,不成;占逐盗、追亡人,得而复失之;占病者,笃;占行者,不发;占来者,亟至;占市旅者,自当;占物,黄、青;占战斗,不合。
斗:斗乘斗,门有客,所言者末事、急事也。占狱讼,不胜;占约结,不成;占逐盗、追亡人,得;占病者,笃;占行者,已发;占来者,未至;占市旅,不吉;占物,白;占战斗,不合。
[危:斗乘]危,门有客,所言者危行事也。占狱讼,疑;占约结,不成;占逐盗、追亡人,弗得;占病者,笃;占[行者],已发;占来者,亟至;占市旅者,自当;占物,杂白;占战斗,吉。
[柳:斗乘柳,门有客],所言者忧病事也。占狱讼,系留,不吉;占约结,不成;占逐盗、追亡人,不得;[占病者],□;占行者,未发;占来者,不至;占市旅,不吉;占物,青、赤;占战斗,不吉。
翼:斗乘翼,门有客,所言者行事也。占狱讼,已;占约结,成;占逐盗、追亡人,得;占病者,有瘳;占行者,已发;占来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青、黄;占战斗,不合。[1]
其余各宿所占内容和排列顺序与此相类,不烦枚举。根据简文来看,每一宿占所列占项都大致相同,其占项主要有:“狱讼”、“约结”、“病者”、“行者”、“来者”、“逐盗”、“追亡人”、“市旅”、“物”、“战斗”等。这些内容出现在占卜书中,表明它们与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该墓葬年代下限为秦二世元年,可知所出日书当行用于秦代晚期,可以视为秦末社会生活的写照。
在这些占项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狱讼”被列为各宿诸占项之首,亦体现出“狱讼”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应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备受关注。所谓“狱讼”,《周礼·地官·大司徒》“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郑玄注云“争罪曰狱,争财曰讼。”贾公彦疏曰:“狱讼相对,故狱为争罪,讼为争财。若狱讼不相对,则争财亦为狱。”占狱讼的征兆,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狱讼案件处理的实况。
从各宿占狱讼所获征兆结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情况:第一类为“不吉”,比如角宿“占狱讼,不吉”,即未能获得吉兆。不吉的含义比较宽泛,据柳宿“占狱讼,系留,不吉”可知,遭到系留是不吉之兆的具体表现之一。这类狱讼可能属于刑事案件。第二类为“解”与“不解”,比如房宿“占狱讼,解”,氐宿“占狱讼,不解”,箕宿“占狱讼,急,后解”。这里的解大约是和解之意,不解即未能达成和解。解与不解的征兆表明当时存在通过调停达成和解的方式来处理狱讼纠纷的做法。第三类为“胜”与“不胜”,比如尾宿“占狱讼,胜”,斗宿“占狱讼,不胜”。这里的胜应即胜诉,不胜即败诉。胜与不胜的征兆表明这类狱讼是由官府判决的。第四类为“疑”与“已”,比如危宿“占狱讼,疑”,翼宿“占狱讼,已”。已应是顺利结正之意,疑则意味着疑难不决,表明当时存在疑狱的情况。
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中亦包含“卜狱讼系囚”的内容,不过多是残篇断简,只是零星可见,比如《音律贞卜》256简:“夹钟、毋射、应钟皆曰:请谒难得,有为难成,取妇嫁女可也,疾人危,系囚难出。”257简:“大吕、姑洗、中吕、林钟皆曰:请谒得,有为成,取妇嫁女者吉,病者不死,系囚者免。”还有几枚残亦涉及相关内容,如310简:“以吉卜其……犬主人,系囚不免”,372简:“取妇嫁女不吉,疾人死,系囚者不免。”简263:“祠有不治者。卜狱讼系囚不吉。”[2]
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亦包含卜问系囚的内容,其卜问结果主要有“系,亟出”、“系,久不已”、“系,不免”等。[3]根据《史记·龟策列传》所述,“卜系者出不出”亦是神龟占的主要占项之一,其卜问的结果有:“系者重罪不出,轻罪环出”、“系者出”、“系者解”、“系者不出”、“系者未出”、“系者久毋伤”、“系者毋罪出”、“系者出,有忧”、“系久不抵罪”、“系留毋伤,环出”、“系留祸罪无伤出”、“系留毋罪难出”、“系留有罪”、“系留有抵罪”、“系难出,毋伤也”,等等。[4]在尹湾汉墓简牍《博局占》中,“问系者”亦是五大占项之一,占测的结果包括“疑未可知”、“轻易解”、“治急”、“事决”、“有喜”、“见深难决”、“毋罪”、“久毋伤解”等。[5]
总之,在日书等占卜之中出现“占狱讼”、“问系者”等占卜事项,大体上反映出当时诉诸官府和法律来解决纠纷,在民间社会是一种比较广泛的现象。而在随州孔家坡汉墓所出《日书》简牍中,则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民间社会对刑罚制度的谙熟和了解。其中有一幅用于占卜的“天牢”式盘图画,图画共有四圈,将六十记日干支按一定规律分属五栏。其下附文字内容为:
此天牢。系者:[6]一曰除;二曰赀;三曰耐;四曰刑;五曰死。居官、宦御:一曰进大取;二曰多前毋句(后有脱文);四曰深入多取;五曰臣代其主。
整理者指出,这里的天牢,指天牢星。《史记·天官书》“赤帝行德,天牢为之空”,《正义》:“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不对中台,主秉禁暴,亦贵人之牢也。”图画之下所附文字内容中的五“曰”,与图画的五栏可能存在一定关系。图可能是供查找“曰”所在的日子,亦即“天牢”所系之日。图上六十干支记日载排列上按一定规律换栏。[7]这件式盘的具体使用方法,或许已经无法复原。不过根据其所附文字内容来看,很可能叙述的是这种式盘的用途而不是使用方法,即这件式盘有可能是专门用于针对“系者”和“居官、宦御”进行占卜的。所谓系者,很可能就是指系于狱中的囚徒。因为在时人看来,天牢星与系囚密切相关,比如《汉书·天文志》“邪正存亡,虚实阔陿”注引孟康曰:“虚实,若天牢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之属也。”[8]如果此说不误的话,则“一曰除,二曰赀,三曰耐,四曰刑,五曰死”,是为系囚占卜所得的五种结果,正好与免除、赀罚、耐刑、肉刑、死刑等刑罚相应。
降至汉代,法律的权威性得到进一步确立。一方面,民众熟知许多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的第一个案例记载,汉高祖十一年,南郡夷道男子毋忧被县尉派遣去充当屯卒,毋忧中途逃亡,一位名叫九的发弩卒将其逮送归案。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毋忧即引用相关的法律条文为自己的逃亡行为辩护,他说:“蛮夷大男子岁出五十六钱以当徭赋,不当为屯,尉窯遣毋忧为屯,行未到,去亡。”夷道长官诘问毋忧说:“律蛮夷男子岁出賨钱,以当徭赋,非曰勿令为屯也,及虽不当为屯,窯已遣,毋忧即屯卒,已去亡,何解?”毋忧说:“有君长,岁出賨钱,以当徭赋,即复也,存吏,毋解。”由此可见,毋忧不但熟知“蛮夷男子岁出賨钱以当徭赋”的法律规定,而且还能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解释。夷道长官认为“蛮夷男子岁出賨钱以当徭赋”仅是针对徭赋义务的免除,不包括充当屯卒之责。而在毋忧看来,“岁出賨钱以当徭赋”则意味着复除包括屯戍在内的所有义务。面对毋忧的解释,夷道长官无法给予有力辩驳,于是将其作为疑罪上报南郡。南郡司法官吏对于此案的判决则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毋忧应当被处以腰斩,另一种则认为毋忧无罪,不应当受处罚。最后南郡不得不将其作为疑罪上报中央的廷尉。虽然廷尉最终裁决毋忧有罪应当腰斩,但毋忧对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熟知则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方面,民众普遍懂得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土简牍资料有不少涉及债务、田产、人命等内容的法律诉讼文书案卷,即可为证。居延汉简中著名的“候粟君责寇恩册事”简册,即是关于一桩涉及财物纠纷的民事诉讼案的卷宗。在此案中,身为甲渠候的粟君并没有依仗自己的权势和职务向寇恩逼债,而是通过法律程序提起诉讼。而寇恩作为一介平民,也毫不畏惧,敢于和甲渠候粟君这样的官吏对簿公堂。而居延县让双方当事人根据对方的起诉或答辩提供各自的证辞,则表明民事案件的主体比较平等,当时法律和司法制度也较完备。[9]
汉简中还有不少债务文书,根据文书内容可知,在发生借贷等债务行为时,双方会订立契约,形成债券,并将一份交由官府留存,官府则将这些债券汇总成册集中保管,此即“责券簿”。债券实物如居延汉简26.1:“建昭二年闰月丙戌,甲渠令史董子方买鄣卒□威裘一领,直七百五十,约至春钱毕已,旁人杜君嶲。”遇到欠债者不能如期偿还债务时,债主会向官府提起申诉,请求官府追债,此即“自言”债务文书,比如居延汉简217.15,217.19:“吞远隧卒夏收自言责代胡隧长张赦之,赦之买收缣一丈,直钱三百六十。”3.6:“隧长徐宗自言责故三泉亭长石延寿茭钱少二百八十,数责不可得。”官府受理申诉之后,会向负债者所在地签发公文,请求调查核验、代为收债,此即索债文书。比如居延汉简35.4:“第廿三候长赵倗责居延骑士常池马钱九千五百,移居延收责重·一事一封,十一月壬申令史同奏封。”官府索债时通常要以债券簿为依据,制作成牒书,一并发往负债者所在地。比如506.9A:“元延元年十月甲午朔戊午,橐佗守候护移肩水城官吏自言责啬夫荦晏如牒。书到,验问、收责、报,如律令。”[10]负债者所在地接到相关文书之后,会进行调查核验并将结果及时回复,比如居延新简E.P.T59:8:“贷甲渠候史张广德钱二千,责不可得,书到,验问,审如猛言,为收责言,谨验问广德,对曰:乃元康四年四月中,广德从西河虎猛都里赵武取谷钱千九百五十,约至秋予。”[11]如果情况属实,官府会责令负债者及时偿还。对于一时无力偿债者,亦可另行商议还债期限或以财物抵债。对于吏员的欠款,有时则强制其以俸钱偿付,比如居延汉简279.17:“出吞远士吏平四月奉,四月庚戌令史博付仓曹史孙卿,偿具丽卒陈□”。这些债务文书的大量存在,反映了吏卒诉诸官府追讨债务的普遍做法。
在遇到发生纠纷时,民众亦多诉诸官府,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比如《汉书·于定国传》所载著名的东海孝妇案和《后汉书·循吏列传》所载上虞寡妇案,表明两汉乡里村妇,也已经知道直接向官府告诉刑讼之事。《汉书·王尊传》记载王尊为京兆尹,“尊出行县,男子郭赐自言尊:‘许仲家十余人共杀赐兄赏,公归舍。’”对待这种仇杀事件,民众不是像汉初那样求诸游侠豪杰处理,而是直接上诉官府,请求介入。说明在处理刑讼案件上,官府权威正在逐步取代游侠豪杰,法律意识已经深入人心。[12]
即便是在复仇风俗的影响下,不少人出于“私义”走上复仇之路,但是在完成复仇行为之后,许多复仇者主动选择就“公法”,向官府投案自首,接受国家刑律的制裁,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法律意识。比如郅恽在替友人董子张报了杀父之仇后,主动诣县自首,县令大约因赞赏郅恽的行为而迟迟不作答复,于是郅恽对他说:“为友报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义也。亏君以生,非臣节也。”说完这些话之后,自行“趋出就狱”。[13]
赵娥在报父仇之后,亦诣县自首,曰:“父仇已报,请就刑戮。”“禄福长尹嘉义之,解印绶欲与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后来因遇大赦,得以免罪。[14]
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亲一同前往集市,途中遇一醉客侮辱其母,毋丘长一怒之下杀死醉客后逃亡,安丘县派人一路追踪,至胶东将其捕获,胶东相吴祐对毋丘长说:“子母见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虑难,动不累亲。今若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刑若不忍,将如之何?”毋丘长“以械自系,曰:‘国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虽加哀矜,恩无所施。’”于其冬被处死。[15]毋丘长虽杀人逃亡,但在追逮所及时能坦然接受“国家制法”,表明他对于杀人的法律后果有着清楚的认识。
盛道之妻媛姜的故事则表明,她十分了解“聚众起兵”定会被处死的法律后果。《后汉书·列女传·盛道妻传》载,建安五年,益部扰攘,盛道聚众起兵,失败之后,夫妻二人皆被执系,按律当会处死。当晚妻子媛姜告诉盛道说:“法有常刑,必无生望,君可速潜逃,建立门户,妾自留狱,代君塞咎。”于是为盛道解开桎梏,让他带上钱粮和儿子一起逃走。估计他们走远之后,媛姜“以实告吏,应时见杀”。
当然,除了尊重法律、利用法律之外,秦汉时代亦存在反抗法律的情形。犯罪逃亡、躲避制裁,属于消极的个人反抗。亦有不惜自杀或自残以逃避徭役、兵役的极端行为,如秦始皇时期连年征战,使得“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16]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有“贼伤人,及自贼伤以避事者,皆黥为城旦舂”的法律条文,这里所谓“自贼伤以避事”,即是故意自残以逃避役使之事。[17]著名的陈胜、吴广率领戍卒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则是对“失期法斩”的集体反抗。另外秦汉社会中的“群盗”现象亦属对法律的集体反抗行为。这些来自民众的反抗尤其是集体反抗,有时会促使法律变革乃至社会变迁。
二、法律诉求
汉代民众对于法律的诉求主要体现在对执法官吏的态度和评价之中。大体说来,注重教化、留意民生、执法宽平的官吏最为汉代民众所拥戴和信爱,通常也得到皇帝的赏识。比如兒宽为左内史时,“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后来兒宽又“表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襁属不绝,课更以最。”正是因为采取切实的措施解决民生疾苦,执法务行宽缓,审理狱讼时能够体恤人心,所以兒宽得到“吏民大信爱之”,皇上也对他愈加赏识。[18]
黄霸为河南太守丞时,“处议当于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爱敬焉。”宣帝即位之后,“闻霸持法平,召以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后来黄霸出任颍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后诛罚”,“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黄霸任颍川太守前后八年,郡中大治,后来天子下诏称扬曰:“颖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乡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不久黄霸被征为太子太傅,迁任御史大夫。[19]
朱邑少时为庐江舒县桐乡啬夫,“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后来官至大司农,“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延敬焉。”朱邑死后葬于桐乡,桐乡之民“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20]这是死后为之立祠,表达追思与怀念。
汉代民众对于爱民良吏的最高礼遇则是生为立祠、立庙或者立碑。尤其对于那些断狱公平,能够使受到处罚之人“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衔怨而受罪”[21]的执法良吏,更是尊崇有加,以至于“为之生立祠”。《汉书·于定国传》载,东海人于定国之父于公“为县狱史,郡决曹,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为之生立祠,号曰于公祠。”于公也因此成为执法良吏的典范和象征,成为人们称引的参照,比如颍川郭躬“为决曹掾,断狱至三十年,用法平。诸为弘所决者,退无怨情,郡内比之东海于公。”[22]另如韦义“为广都长,甘陵、陈二县令,政甚有绩,官曹无事,牢狱空虚”,“广都为生立庙。及卒,三县吏民为义举哀,若丧考妣。”[23]杨仲续“拜祁令,甚有德惠,人为立祠。”[24]荀淑先后任当涂长、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称为神君”,“二县皆为立祠。”[25]童翊“除须昌长。化有异政,吏人生为立碑。”[26]
汉代两位执法官吏的母亲对儿子的态度和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们反对执法官吏“多刑杀人”,期望执法官吏重人命、多活人的诉求。《汉书·雋不疑传》载,雋不疑在青州刺史任上,成功发觉和惩治了交结郡国豪杰意图谋反的齐孝王之孙刘泽等人,得以擢拜为京兆尹。“京师吏民敬其威信。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语言异于他时。或亡所出,母怒,为之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汉书·严延年传》载,严延年为河南太守时,致力于摧折豪强,“然疾恶泰甚,中伤者多,尤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流血数里,河南号曰‘屠伯’。”某年岁末,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来探望他,刚至洛阳就见到处决罪囚之事,于是她便留止都亭,不肯进太守府。严延年到都亭拜谒,她也闭门不见,严延年在门外“免冠顿首”,过了很长时间,母亲才见他,并责备他说:“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严延年顿首谢罪,亲自为母亲驾车,将其接至府舍。腊祭之后,母亲即返回东海,临走前他告诫严延年说:“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东归,埽除墓地耳。”一年多之后,严延年被府丞告发,“坐怨非谤政治不道弃市”。根据严延年之母责备他的话语中可知,在她看来,“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为民父母的郡守要在“仁爱教化”以“全安愚民”,而不是“乘刑罚多刑杀人”以“立威”,否则自身也难逃“被刑戮”的下场。
对于滥施无辜的官吏,民众亦会通过集体告诉表达不满意愿。比如酷吏田广明之兄田云中为淮阳守时,诛杀过重,导致民众不满,于是“吏民守阙告之”,田云中因此受到惩处,“坐弃市”。 [27]
虽然民众通常期望法律宽缓、执法公平,反对滥杀无辜,但是那些敢于重刑摧折侵渔百姓的地方豪强大姓的官吏,往往亦得到民众的赞赏和认同,至以歌谣的方式传颂其事迹。比如《太平御览》卷二六八引《会稽典录》曰:“徐弘,字圣通,为山阴令。县俗刚强,大姓兼并。弘到官,诛剪奸桀,豪右敛手。商旅路宿,道不拾遗。童歌之曰:‘徐圣通,政无双,平刑罚,奸宄空。’”[28]
三、参与意识
汉代民众的法律参与意识通常体现在对重要案件的关注、议论和态度上,以及集体为受到不公判决的当事人“讼冤”等行为之中。比如魏相任河南太守时,“禁止奸邪,豪强畏服”。“后人有告相贼杀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将军,自言愿复留作一年以赎太守罪。河南老弱万余人守关欲入上书,关吏以闻。”[29]胡建为渭城令,“治甚有声”,因至盖长公主府第追捕受其私夫丁外人唆使射杀京兆尹的犯人,引起盖长公主不满,“使人上书告建侵辱长公主,射甲舍门。知吏贼伤奴,辟报故不穷审。”最初大将军霍光“寝其奏”,后来霍光生病,与盖长公主和丁外人交好的上官安代为听事,“下吏捕建,建自杀。吏民称冤,至今渭城立其祠。”[30]赵广汉为京兆尹时,“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长老传以为自汉兴以来治京兆者莫能及。”后来因与丞相生隙,告发丞相之罪有不属实之处,司直萧望之劾奏:“广汉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节伤化,不道。”宣帝恶之,“下广汉廷尉狱,又坐贼杀不辜,鞠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这些罪名上报之后,得到天子认可。获知这一消息之后,“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或言‘臣生无益县官,愿代赵京兆死,使得牧养小民。’广汉竟坐要斩。”“广汉虽坐法诛,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职。百姓追思,歌之至今。”[31]
韩延寿历任颍川太守、东郡太守、左冯翊等职,推行礼义教化,恩信遍著,深得吏民爱戴,“吏无追捕之苦,民无棰楚之忧,皆便安之。”“在东郡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在左冯翊“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复以辞讼自言者。推其至诚,吏民不忍欺绐。”后来韩延寿因政争而坐罪弃市,“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车毂,争奏酒炙。延寿不忍距逆,人人为饮,计饮酒石余。使掾史分谢送者:‘远苦吏民,延寿死无所恨。’百姓莫不流涕。”[32]元帝时期,京兆尹王章借日食之机,上书弹劾帝舅大将军王凤专权蔽主,“宜废勿用,以应天变”。王章因此受到王凤构陷,罪至大逆,死于诏狱。“章既死,众庶冤之,以讥朝廷。”后来王凤不得不听从杜钦的劝说,采取挽救措施、平息舆论。[33]
集体诣阙上诉、为人讼冤的行为,可谓汉代民众法律参与意识的直接体现,也是汉代民众法律意愿的直接表达。比如,汉哀帝时有千余名太学生集体救援鲍宣之事。《汉书·鲍宣传》载:“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官属以令行驰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闭门不肯内。宣坐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髡钳。”
光武帝时期,大司徒欧阳歙“坐在汝南臧罪千余万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闻狱当断,驰之京师,行到河内获嘉县,自系,上书求代歙死。”[34]明帝时期,会稽太守第五伦,深得百姓爱戴,“永平五年,坐法征,老小攀车叩马,啼呼相随,日裁行数里,不得前。伦乃伪止亭舍,阴乘船去。众知,复追之。及诣廷尉,吏民上书守阙者千余人。是时显宗方案梁松事,亦多为松讼者。帝患之,诏公车诸为梁氏及会稽太守上书者勿复受。会帝幸廷尉录囚徒,得免归田里。”[35]桓帝时期,冀州刺史朱穆获知宦官赵忠之父归葬时丧葬僭制,于是下郡案验。“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而收其家属。帝闻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桓帝览奏之后,赦免了朱穆。[36]桓帝延熹年间,度辽将军皇甫规因拒绝宦官徐璜、左悺等人的索贿,受到诬陷,“以余寇不绝,坐系延尉,论输左校。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会赦,归家。”[37]
史弼迁任河东太守,因拒绝中常侍侯览的请托,使侯览大怨,“遂诈作飞章下司隶,诬弼诽谤,槛车征……及下廷尉诏狱,平原吏人奔走诣阙讼之……弼遂受诬,事当弃市。”魏劭变卖家产,诈为家僮,贿赂侯览,使史弼得“得减死罪一等,论输左校。”时人或讥曰:“平原行货以免君,无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闳、散怀金。史弼遭患,义夫献宝。亦何疑焉。”于是议者乃息。[38]民众对于史弼案的不同态度,实际上也体现出了不同的诉求。平原吏人知其受侯览诬陷而获罪,于是积极参与救援,为之奔走,诣阙讼之,但诣阙诉讼没有能够改变判决结果。最终是魏劭变卖家产、贿赂侯览,使得史弼得以免除死罪。但这种行贿免罪的行为却受到了部分时人的讥讽。
除了集体诣阙而讼之外,个人诣阙告诉的行为在汉代亦十分常见。如齐太仓令淳于公之女缇萦诣阙救父,并成为文帝下诏废除肉刑的契机,即是卓有成效的实例。
作者信息:
邬文玲,女,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100732;
电话:13439593963
wwlhis@yahoo.com.cn
[1] 湖北省周梁玉桥博物馆:《关雎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第104—117页。
[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年。
[3]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84—185页。
[4] 《史记》卷一二八《龟策列传》,第3241—3251页。
[5]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第126页。
[6] 整理者将此句读作“此天牢系者”,晏昌贵改作“此天牢。系者”,可从,参见其所著《孔家坡汉简<日书>天牢篇笺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93—310页
[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74—175页。
[8] 《汉书》卷二六《天文志》,第1273页。
[9] 参见张建国:《居延新简“粟君债寇恩”民事诉讼个案研究》,收入氏著《帝制时代的中国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37页。
[10]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609页。
[1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
[12] 参见邹水杰:《两汉县行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3页。
[13] 《后汉书》卷二九《郅恽传》,第1027页。
[14] 《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庞淯母传》,第2797页。
[15] 《后汉书》卷六四《吴祐传》,第2101页。
[16] 《史记》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8页。
[17]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18] 《汉书》卷五八《兒宽传》,第2630页。
[19]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黄霸传》,第3627页。
[20]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朱邑传》,第3635页。
[21] 《汉书》卷八六《王嘉传》,第3501页。
[22] 《后汉书》卷四六《郭躬传》,第1543页。
[23] 《后汉书》卷二六《韦彪传附族子义传》,第921页。
[24] 《后汉书》卷三○上《苏竟杨厚列传》注引《益部耆旧传》,第1047页。
[25] 《后汉书》卷六二《荀淑传》,第2049页。
[26]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童翊传》,第2482页。
[27] 《汉书》卷九○《酷吏传·田广明传》,第3665页。
[28]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第1256页。
[29] 《汉书》卷七四《魏相传》,第3134页。
[30] 《汉书》卷六七《胡建传》,第2912页。
[31] 《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第3205页。
[32]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自强东路759号交通运输大厦2-2403号
电话:029-81616443 邮箱:qwyjs221@163.com 邮编:71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