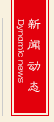总有考据帝选择仰望星空 | 七夕的另一种姿势
发布人:中国秦文研究会秦文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6-08-10 10:49 点击率:1477
遥看牵牛织女星
七月七,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络绎时光中,原本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子,但是,因为有了牛郎织女的故事,这一天,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日子。“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千古以来,诗人们吟哦不绝的七夕诗篇,更为这个日子增添了一层哀艳的诗意,这种诗意和伤感,就像一片朦胧而凄美的月光,自古迄今,绵绵不绝,一直笼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上。
大概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自己懵懂初开的某一年七夕,听自己的母亲,或者祖母,或者外婆,或者伙伴,讲过牛郎织女的故事。故事听完了,你或许会在大人的指点下仰望夜空,在灿烂的银河边找出满天繁星中最明亮的那颗星,那就是织女,织女边上还有两颗较暗的星,和织女鼎足而处,正组成了一个纺车的形状,银河的东边,也有一大两小三颗星,中间那颗明亮的就是牛郎,牛郎两边那两颗暗的就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这样从牛郎织女的故事中,初次领略了爱情的珍贵和人世间的愁滋味。
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如此动人,这个故事的流传又是如此久远,而且,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故事把人间的悲欢离合和天上的星象联系起来,透露出一股子其他民间故事所没有的神秘气息和传奇色彩,因此,自古以来就引来学者的好奇,近世以来,更有中外学者为探究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作了不少大块小块的文章。且近来因为受西方情人节的煽动,有一班忧国忧民的民俗学者和一些心思活络的商人,也开始打起中国情人节的主意,七夕就被这些好人们一眼看中,文人的鼓噪加上商人的炒作,近年来七夕这个本来久已被国人冷落的节日好像突然热闹起来了。前不久那个以民族风情和小资情调闻名于世的滇边小城丽江点击查看丽江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还打出招牌说要跟雅典城联合,让欧罗巴的爱神维纳斯和东方的仙子织女结成姐妹,联袂出演,共同把丽江城打造成东方的情人天堂,把中国的七夕打造成中国的情人节。一年当中,多过几个情人节,自然不是坏事,这个世界上,多点柔情蜜意,多几个神仙眷属,总强过到处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和硝烟弥漫的敌意。但是,把七夕当成情人节来过是一回事,本来的七夕究竟是不是情人节则是另一回事,在此情势之下,七夕的来历,真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
牛郎织女的名字,《诗经》时代的诗人们就已经形诸歌吟。只是那时候的牛郎,还不叫牛郎,而叫牵牛,《诗经·小雅》中的《大东》,是一则征夫之歌,一个久离家园的西周男子,黉夜行脚,举目四顾,银汉横斜,繁星满天,在诗中一口气给我们报出了六个星星的名字: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天毕,载施之行。
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
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诗中的汉即银河,而织女、牵牛、启明、长庚、天毕、箕、斗都是星名,可见早在西周时期,那两颗行星就获得了织女和牵牛的名目了,而且,诗称织女“不成报章”,又谓牵牛“不以服箱”,暗示当时民间早就把织女星想象成了一个纺线织布的女子,把牵牛星想象成为一个牵牛拉车的牵牛郎,而且,织女和牵牛并举,也隐隐流露出两者之间脉脉相望的关系。可以想象,在这首诗歌被形诸笔墨之前,在民间,应该早就有与牵牛织女相关的口头传统流传了。
但从这首诗中,我们无法找到牵牛、织女和七月七关联的线索。七月七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古人对星象的关注,也主要是源自星象对于时令的标示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到华夏先民的时间知识或者说岁时知识中去寻找七月七与牵牛织女星之间关联的因缘。《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一篇最古老的华夏时间知识文献,其中系统记载了古人的农时知识,详细叙述了夏历一年十二个月中的农事活动以及与不同时令对应的物候、气象和星象,其内容和作用,就相当于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在《夏小正》的七月和十月记事中都提到织女星,十月与我们的话题无关,撇开不谈,且看其七月怎么说:
七月,秀苇。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秀。汉案户。寒蝉鸣。初昏,织女正东向。时有霖雨。灌荼。斗柄悬在下,则旦。
其中,“秀苇”、“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秀”、“寒蝉鸣”、“时有霖雨”、“灌荼”,所言皆为动、植物的物候,而“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向”、“斗柄悬在下,则旦”所言则皆为星象。
“汉案户”,汉谓银河,银河逶迤横斜,随星空而回旋,一年当中的不同时间,银河的走向各不相同,古人因此根据银河的走向判断时节,当看到银河从南到北横亘夜空,银河的下端正好对着门户的时候,古人就知道,七月已到,该是暑退凉起的初秋天气了。
“斗柄悬在下”,斗指北斗,上古时期,北斗七星靠近北极,璀璨的北斗星回旋于天,就像一个指针,向大地苍生昭示着岁月的流逝。故《史记·天官书》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一方面,由于地球的公转,一年当中,斗柄随季节的轮回而指向夜空的不同方向,因此,在夜晚的同一时刻仰观斗柄的指向,可以判断季节;另一方面,随着地球的自转,斗柄在一夜当中也随时辰的流逝而回旋,因此在一年的特定季节,观察斗柄的指向可以判定时辰。“斗柄悬在下,则旦”即谓此,意味着到了七月,晚上只要看到北极的斗柄垂下来指向北方(下),就知道天快亮了。或者反过来说,如果在拂晓前看到北斗的斗柄垂向北方,就知道该是初秋的七月了。
大概是因为七月处在夏秋之交,正当时令转换的关口,因此,《夏小正》的作者对于七月的天象言之特详,除了银河的走向和北斗的指向之外,又刻意提到织女星象,而正是这条关于织女星的记载,再清晰不过地向我们透露出牛郎织女与七夕之间关系的消息。“初昏,织女正东向”,织女星由一大二小三颗星星组成,其中织女一为0等星,为全天第五亮星,在北方高纬度夜空则是最亮的一颗星星,而且由于织女星纬度较高,一年中大多数的月份都看得见,因此,高悬天顶、璀璨夺目的织女星肯定早就引起古人的注目,并根据它的方位变化作为观象授时的依据之一。织女三星成三角形排列,“织女正东向”的意思是指由两颗较暗的星星形成的开口朝东敞开。“七月,……初昏,织女正东向”,当《夏小正》时代的农人们,在黄昏之后仰望头顶的夜空,看到明亮的织女星出现在深邃的天幕上,散发着柔和的星光,由两颗较暗淡的小星形成的织女星开口朝向正东,他知道,七月到了,秋天来了,该是准备收获的时候了。
七月初昏织女正东乡
织女星朝向东方,东方是什么呢?《夏小正》没说,但古时候的人们只要抬头看去,就会一目了然,黄昏的夜空,在织女的东方稍偏南的地方,在“河水清且涟漪”的银河东岸,不是别的,就是那颗让织女朝思暮想、只能在七夕一会的牵牛星。牵牛和织女分居银河两岸,到了初秋夜晚,由于银河正好转到正南北的方向,直贯头顶的夜空,因此,这个时候,分居河两岸的牵牛和织女正好一东一西,隔着银河,遥遥相望。说到这里,牛郎织女的故事不是呼之欲出了吗?七月黄昏,夜空中这种银河直贯南北、织女高悬天顶、牛女相映成辉的景观肯定给古人留下深深的印象,而“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意象自然就是从这种天象演绎而来。
但故事还没有到此为止。上面的这一番分析,说明了古人为什么会在七月关注牵牛和织女这两颗星,为什么会把牵牛织女的故事和七夕联系起来。可是天上自在运转的星星本自无名,这两颗星分别被命名为牵牛和织女,又有何来历呢?
命名源于意义,人们对事物的命名,基于这个事物对他的意义,而辉映夜空的星象,对于人间的意义,主要是在于其授时功能,即作为时间标示的作用。人类之所以仰望星空,首先是因为斡旋天幕的群星,昭示着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轮回,也标志了节令的转换和农时的早晚,因此,星象对于古人的意义,主要在于其时间性,《易传》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尧典》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皆谓此意。此理古今中外皆然。希伯来人的圣经《旧约·创世记》说,上帝开天辟地、创造万物之后,就在天上布置群星作为划分岁月时日的依据,“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可见希伯来人也是从时间性角度认识和理解星空的。名本乎义,星象因时取义,故由时得名。明乎此理,则应该从星象和农时的关系入手,探究牵牛和织女的来历。
如上所述,在《夏小正》中,“织女正东向”,和牵牛隔河相望,是七月到来的标志。七月处夏秋之交,一入此月,则暑气渐消,凉风乍起,这个时候,女人就要开始忙碌了,纺线织布,准备寒衣,迎接即将到来的肃秋和严冬。《诗经·豳风·七月》开篇就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就道出了此意:“七月流火”,黄昏时候,大火星开始向西方地平线坠去,表明秋天开始了,“九月授衣”,九月已是万物肃杀的晚秋,该是穿寒衣的时候了。九月授衣,则必须八月裁制,那么,七月,就该是纺织娘们飞梭织布的时候了。
——《七月》通篇皆言时令,它其实就是周代豳地流传的农时歌谣,诗中又说:
“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鸣,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女子的唇吻声腔犹然在耳,可见此诗出自女性之口,讴歌的主要是女子一年到头的劳作和悲欢。诗的前三章,都是以“七月流火”起兴,表明这首歌很有可能就是古时候的织妇们在七月萤火明灭的夜晚,在灿烂的星光下,一边摇动纺车织布,一边反复吟唱的。天上,织女星光璀璨,地上,纺织娘浅唱低吟,人间天上,相映成辉,那颗照耀着人间纺织娘劳作的明星,因此就被赋予了织女的名称,成了人间织女的守护神。
七夕节乞巧风俗,显然就是源于其与入秋夜绩、女红劳作之间的关联。晋人葛洪《西京杂记》说:“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
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说:
“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七夕之后,妇女开始纺绩裁衣,因此在这一天陈设针线,祈求心灵手巧,既是一种郑重其事的仪式,也是一种劳作季节开始前的心理准备。正是凭借着这种年复一年的乞巧仪式,牛郎织女的故事才代代相传,流传人间。
《荆楚岁时记》说七夕乞巧时要“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此外,东汉崔《四民月令》、晋代周处《周处风土记》、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皆记载有七夕乞巧陈设瓜果祭献牵牛织女的习俗。
七夕何以必须陈设瓜果?
有学者从瓜果联想到“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的诗句,说这种活动象征女性崇拜或生殖崇拜,这未免太“即空见色”、想入非非。其实,这种习俗并无什么神秘意味或象征意味。七夕之所以刻意陈设瓜果,不过是因为七月之时,正是瓜果成熟的时候,《七月》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壶”通“瓠”,即葫芦,又云:“八月剥枣,”《七月》之诗旨在叙农时,诗中特意提到食瓜、剥枣,可见我们的祖先自古就重视瓜、枣成熟的时令意义。七月之后,瓜果飘香,因此,妇女们于七夕聚会之际,陈设瓜果,作为祭祀牛、女的应时之物。其实,这些瓜果名义上是供神,最后终究还是被聚会的人间儿女们自己享用了。正因为七夕与瓜果之间的时令关联,因此,汉代纬书《春秋合诚图》说:“织女,天女也,主瓜果”(《开元占经》引),则在古人心目中,织女俨然成了瓜果的象征。中国传统星象图中,在织女的东边,牵牛星附近,有一组星的名字叫瓠瓜(即西方星图中的海豚座),瓠瓜边上还有一组更暗的星叫败瓜,显然也是古人用为瓜果成熟时节的时间标志的,古人当黄昏之际看到这个星象出现在头顶时,就知道该是断瓠剥枣的时候了,而败瓜的意思大概是说,如果不及时采摘,瓜果就会颓败腐烂。
牵牛之名,未见于《夏小正》,却出现于华夏先民时间知识的另一个重要文献《月令》之中。《月令》载于《吕氏春秋》、《礼记》和《淮南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之中,其内容和形式都与《夏小正》大同点击查看大同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小异,也是按照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叙述每个月的天象、物候、农功、仪式等等。中国传统天文学体系中,把周天沿赤道附近的星带分为二十八宿,即二十八个星象。一年当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二十八宿周回于天际,因此根据每天黄昏或黎明出现于正南方的星象,就可以了解时序之推移,《月令》于每个月皆记载其昏、旦中星(即见于南方的星),即此意。其中仲秋八月的黄昏中星就叫牵牛,“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中”。然而,此牵牛却非彼牵牛,不是那个在银河东岸跟织女隔河相望的牵牛,而是指二十八宿的牛宿。
原来,在古书中,银河边那个牵牛,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河鼓,《史记·天官书》说:“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其所谓牵牛,指二十八宿中的牵牛,而其所谓河鼓,才是银河边的牵牛,故《史记索隐》引《尔雅》说:“河鼓谓之牵牛。”银河边的牵牛何以一星而二名,既名牵牛,又名河鼓,而牵牛之名又何以一名而二星,既指银河边的河鼓,又指二十八宿中的牛宿,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曾成为中国天文学史上一段不大不小的公案。尽管各家对此现象的解释各有千秋,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银河边的牵牛(即河鼓)才是真正的牵牛、最早的牵牛,先民们最早所关注的正是这个牵牛。二十八宿中的牛宿亮度很低,放眼望去,在满天繁星中毫不起眼,根本不会引起农耕先民的关注,因此最初也不会被农耕先民用为纪时的依据。只是后来随着二十八宿系统的建立,由于原先的牵牛星位置比较靠北,远离赤道,而为便于观察,二十八宿必须位于赤道附近,因此,后来的天官就在牵牛的南边临近赤道的星空中,找到另一组星,取代了原先的牵牛,而为了区别,原先的牵牛就被赋予了新的名字。
那么,银河边的这颗星何以被命名为牵牛呢?“牵牛为牺牲。”牺牲指诸如牛、羊之类在祭典上宰杀献神的牲畜。《天官书》所谓“牵牛”,所指自是二十八宿之牛宿,但却也足以表明,牵牛一名的意义是源于牺牲,而这也就意味着,银河边的牵牛亦取义于牺牲。《月令》就提示出牵牛之得名与牺牲之间的时间因缘。牺牲的饲养生长有一定的周期,每一阶段,针对牺牲,都要举行一定的活动,对此,《月令》中有明确的记载:春天,万物孳乳,牲畜繁育,故到了暮春三月,需要统计幼畜的数量,“牺牲驹犊,举书其数”;六月,夏秋之交,草木丰茂,刍秣收割,故“命四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臣民贡献牧草以为养牲之饲料;八月,仲秋之月,正是动物膘肥毛丰的时候,于是天子“乃命宰祝,循行牺牲,”巡视牺牲,察其体量毛色,合规中度的牲畜才能用为牺牲,九月,暮秋之月,牺牲已经长成,故“牺牲告备于天子”;到了腊月岁末,就该是宰牲祀神,举行一年一度的郊天大典的时候了,于是,天子“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飨”。诸神降临,馨享牺牲,降福穰穰,给芸芸众生带来太平和吉祥。八月“循行牺牲”,而此时昏见南方的中星,作为视牲之月的时间标志,被命名为牵牛,可谓顺理成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按照上文的分析,织女为七月之星,被作为秋天到来和女功伊始的标志,而牵牛为八月之星,被作为视牲和祭献的标志,两者时间不同,事义亦别,似乎毫不相干,岂不是与七夕故事和民俗中两者息息相关的关系相矛盾吗?其实,当七月,织女星升上天顶并垂顾人间织妇之时,牵牛星就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牵牛与织女之间,盈盈一水,原本相去不远。七月过后,当一度高悬天顶的织女离开天顶向西倾斜时,牵牛星就后来居上,升上最高点了,岁序也就随之进入仲秋八月了。多情的牵牛就是这样在织女身后紧追不舍,然而天命难违,这对生死冤家之间永远间隔着那段咫尺天涯的时、空距离,“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以上所述,可见七夕故事和民俗的各个主要环节,都可以由其与岁时的关系得以解释:织女之名织女,因其为纺绩之月的标志;牵牛之名牵牛,则因其为视牲之月的标志;当此夏秋之交,织女星和牵牛星先后双双升上中天,隔河相望,牛女七夕会银河的故事即由此而来;七夕穿针乞巧,不过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纺织季;乞巧之时陈设瓜枣,则是因为此时正是瓜熟蒂落的季节。民间传说,牛郎织女良宵一度,依依惜别之际,织女都会伤心落泪,泪水化作雨水,因此,每到七月七,天上总会飘下一阵绵绵细雨。七夕的雨水自然不是来自织女的泪腺,七夕之所以多雨,不过是因为初秋七月,正是中国大地连绵秋雨开始的时候,《夏小正》说:“七月,……时有霖雨。”《月令》七月说:“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可见古人早就对夏秋之交多雨的气候特点了然于心。总之,七夕故事的每一个关目都能在古人的时间感中找到源头,天上的星星、人间的织女、初秋的阴雨以及成熟的瓜果,都因其在时序中的同时呈现而被联系起来,被赋予相同的时序意义,被编织于同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
时间性对于人类知识和叙事的奠基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时间,作为大自然恒久不变、周而复始的节律,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生计作息,也引导着人们的认识和叙事,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时间与其说是人类认知和度量的对象,不如说是人类理解和度量万物的可能性条件。时间川流不息,万物生生不已,世间万物都在时间的长河中沉浮隐现,并因此进入或者退出人类的生活和视野,因其在时间这一宏大节律中所出现的不同关口,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被归于不同的认识范畴,被纳入不同的故事情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时间,或者说大自然的节律,就是造物造化众生的脚本;“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传》),浩瀚的星空,苍茫的大地,就是这个脚本搬演的舞台;“天地万物,化醇”(《易传》),物类熙熙,众生纷纶,则是这个舞台上周而复始重复上演的戏剧。每年七夕,牛郎织女天河会,不过是这场戏剧中一个哀婉多情的片断而已。
七夕故事和风俗的时间性,表明它原本只是一个秋天的节日,七夕故事所蕴含的意义,也不过是时令转换、秋天开始的消息,尽管有缠绵悱恻、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但七夕却初与爱情无关。七夕,拉开了秋天的序幕,秋风起兮,繁华落尽,万物萧条,令人黯然神伤,因此,七夕与其说是情人的节日,不如说是一个伤情的日子,与其说是一个令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日子,不如说是一个自古多情伤离别的日子。因此,在古人的观念中,七夕对于婚嫁,并非一个吉利的日子,牛郎织女的爱情,也并没有花好月圆的意味。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占卜简书《日书甲种》就有以牛郎织女为占的条目,一条说:“丁丑、己丑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另一条说:“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可见,在古人心目中,七夕故事,对于爱情和婚嫁而言,原本是凶多吉少的“下下签”,是抽不得的。
时下国人炒作七夕情人节概念,原因之一是为了和西方的情人节抗衡,用心可谓良苦,然而,把七夕当成情人节,可谓数典忘祖。其实,中国原本是有自己的情人节的,它和西方的圣瓦伦丁节一样,不在秋天,而在春天。在古代,包括春分、花朝、春社、清明、上巳等等在内的春天节日,除了其特有的与农事、祭祀有关的仪式内容之外,无一不是风情摇曳的爱情节日,且不说自古以来那些在春天节日上吟唱的诗篇中流露出来的无边风月,翻翻宋明话本、元人戏文,那些多情的才子佳人们几乎无一不是在清明上巳、踏青游春的游戏场上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的。说到底,万物盛开、摇荡性灵的春天才是滋生爱情的季节。
本文转自活字文化